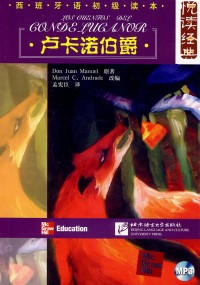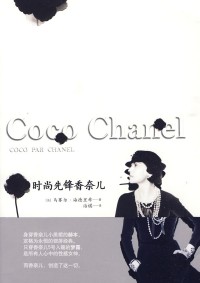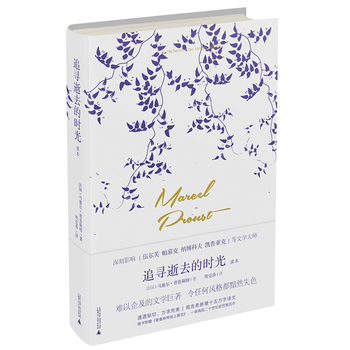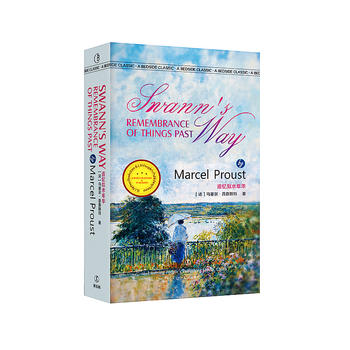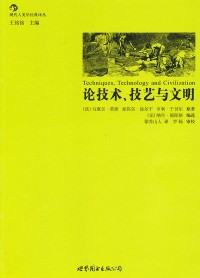共找到 280 项 “Marcel”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Don Juan Manuel原著;Marcel C. Andrade改编;孟宪臣译
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卢卡诺伯爵》,成书于1335年,被认为是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 时代前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该书作者堂·胡安·曼努埃尔精心编写了 50多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因卢卡诺伯爵向他最信任的顾问帕特罗尼奥 咨询解决人生中遇到的困境而引出,帕特罗尼奥通过讲述故事为卢卡 诺伯爵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故事寓意深刻,深入浅出。本书是《卢 卡诺伯爵》的改编版,选入了《卢卡诺伯爵》中1 5个最受读者喜爱的 故事。学习者可以充分感受到西班牙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幽默、智慧以 及哲理。 改编版的《卢卡诺伯爵》专门为初级西班牙语学习者量身定做。 每个故事都有读前思考,鼓励学习者使用已有的知识对故事的内容进 行猜测;故事后面的阅读理解练习供学习者检查阅读效果。 练习可供教师组织课堂讨论使用。故事结尾处的一小 段文字凝炼总结了故事蕴含的人生哲理。权威、详尽的注释,包括出 处注释和历史文化背景注释极大地方便了学习者阅读;书后的词汇表 和参考译文帮助学习者查找和使用。
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盲人领路童》,成书于1554年,给读者描绘了一幅16世纪西班牙的 生活画卷。故事由一个贫穷的男孩拉萨罗讲述。《盲人领路 童》是西班牙黄金时代发表的流浪汉小说中最受人欢迎的作品。 拉萨罗为了谋生,侍奉过不少主人,这些主人都是16世纪各社会阶层 的典型代表,他们让拉萨罗体会到了那个世纪生活的残酷、社会的腐败以 及虚伪。尽管生活环境十分艰难,拉萨罗还是敏锐地观察着人生。拉萨罗 这个形象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怀念的角色。 改编版的《盲人领路童》专门为初级西班牙语学习者量身定做。每个 故事都有读前思考,鼓励学习者使用已有的知识对故事的内容进行猜测; 故事后面的阅读理解练习供学习者检查阅读效果;练习可供 教师组织课堂讨论使用。书后的词汇表和参考译文供学习者查找和使用。
简介:This monumental reference resourc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field of syntax as it has been studied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or so. Made up of 77 extensive case studies written by 80 of the world s leading linguists, it gives a complete overview of the empirical fact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gleaned in syntactic research in recent decades. Under the editorial direction of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this comprehensive multi-volume set comprises case studies commissioned specifically for this Companion. Contributors are drawn from an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restigious linguists, including Joseph Emonds, Sandra Chung, Susan Rothstein, Adriana Belletti, C.-T. James Huang, Howard Lasnik, and Marcel den Dikken, among many others. Each set features an accessible alphabetical structure, with an index integral to each volume. The entire Companion is also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on the accompanying CD-Rom. Published within the prestigious Blackwell Handbooks in Linguistics series, this significant reference work can be relied upon to deliver the quality and expertise with which this series - 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linguistics list - is associated.
作者: (法)M.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著;李恒基等译
简介:本书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文学创作上的新观念和新技巧,小说以追忆的手段,借助超越时空的潜在意识,不时交叉地重现已逝去的岁月,从中抒发对故人,往事的无限怀念和难以排除的惆怅。这种写法不仅对当时小说写作的传统模式是一种突破,而且对日后形形色色新小说流派的出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文共同题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作者: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著;李恒基[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8
简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 小说以回忆的形式对往事作了回顾,有童年的回忆、家庭生活、初恋与失恋、历史事件的观察、以及对艺术的见解和对时空的认识等等。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凭着智慧和想象力,使时间变得具体、生动、完美。它就像一首由多种主题构成的交响乐,爱情、嫉妒、死亡、回忆、时光,时而交叉重叠在一起,时而又游离开来,然而在宏观上,整个作品浑然一体,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公认为文学创作的一次新的尝试,开意识流小说之先河。
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出版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
简介: 在「後現代(主義)」一詞已充斥於文化論述,乃至於日常語言的今天,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校區的伊哈布.哈山教授收錄於本書的十篇論文,彷彿一次次精采的批判性演出,構成了理解文學後現代主義的最佳參考依據。作為後現代主義最早的年代紀學者之一,哈山對這個術語的得以逐漸被接受,貢獻可能超過任何其他批評家。本書鋪陳作者本人對後現代主義的思維發展歷程,探索這個概念所經受的各種磨難與考驗,並檢討有關的論辯,足以讓讀者領受一個文化進行自我了解時深沈、豐沛的一面。 《後現代的轉向》 導讀 在晚近有關後現代的理論探討中,哈山所佔的位置並不十分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即使到了八0年代,哈山還是堅守某種文學本位的「沈默批評」的立場,與主要辯論中各種學科知識與政治立場相互激盪的鬧熱氣氛顯得格格不入。這並不是說,哈山的討論毫無價值;相反的,透過哈山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值得檢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某些後現代理論的基本觀念仍然是息息相關的。 我必須先就「沈默批評」的意義,稍作說明。沈默批評是哈山所謂沈默文學的延伸。在哈山的心目中,西方文學的主流是「從形式走向反形式」,而形式的作用是透過作品語言與藝術規格的操演來保證意義的傳達,所以走向反形式也就是走向沈默,切斷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把文學變成一種高度自律的,內顯(imminant)於文字當中的半神祕經驗。同樣的,哈山心目中的理想批評也保有高度自律的傳統承遞(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它的發展動力來自某種內在的規律。所以晚期的哈山特別強調批評或文化理論必須抗拒來自非文學部門的解釋規範,避免沾染特定的政治立場,不向任何意識形態靠攏。這個立場代表了人文主義傳統的一種典型。可以想見,在一般文學研究者當中,哈出的說法還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 如果我對哈山立場的解釋可以成立,這裡面至少牽涉到兩個問題。其一,文學研究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這種觀念代表的是學科分立的韋伯式現代理性,豈不是大大違背了哈山自己強調的反目的,反連續,反主體的後現代精神?其二,哈山並不否認後現代是產生於「西方社會和它的文學」中的現象,甚至有文學思潮是後現代社會「一個獨特的、精英的方面」的說法。那麼語言文字顯然並不僅是以沈默、憤怒、抗議來面對(規格化的)外在環境,而是在一定的層面上準確的反映,或者說模擬了其他社會、文化部門的現實。 這兩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文學的兩種發展方向的衝突:文學應該秉持抗議精神,嚴守內在的規律,走向社會狀況的對立面,還是接受下層結構的決定,撤除界限,回歸現實的同質面?或者說,文學應該成為社會的監察院,還是社會的存查院?第一種方向本於求真實、求自主等原則,當然具有強烈的現代精神,第二種方向則似乎具有後現代平淺化、反等級、反創造的意味。這裡並不是說,哈山的講法有矛盾:後現代是現代的延伸或修正,或者後現代與現代可以並存,或者兩者皆是,本來就是哈山一再強調的基本立場。我也不想引用辯證關係、相對自律之類的說法,來為兩種傾向強作連繫。另外,這也不是語言或翻譯意思不準確所造成的問題,雖然我們必須記得,postmodernism具有從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現象到後現代症等等的多重涵義。這裡想指出的重點是:哈山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抹除」了這兩種方向的衝突。不是化解,也不是調和,甚至不必動用互補、延伸等觀念;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忽然發現,監察院其實就是存查院。 或許我們可以對哈山的思考路線作一個外繫式的說明(雖然這不合強調內顯的後現代精神)。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真偽、善惡是十分確定的,並不需要有一個專責批判或異議的部門存在。而當這個涵括社會整體的確定性喪失的時候,文學以及其他現代學科就從這個整體獨立出來,接收了確定意義的責任。也就是說整體所失去的確定性,是以窄化、深化的方式,由部分收回來。哈山顯然認為這個分裂、離散的過程一旦開始,就很難終止。所謂一切整體都是專制、極權,便是說整體的意義是用確定的規矩來掩蓋不能確定的真實。社會整體的價值既然難定,文學整體、作品整體、作家整體等等何能獨善其身?任何由整體獨立出來的次整體遲早都會被原來的整體同質化而落入被懷疑的命運。於是不確定的範圍愈來愈大,提供確定功能的對立面則愈來愈緊縮。可以想見,這個過程發展到最後,扮演對立角色的自律部門終會完全失去存在空間:不斷懷疑的結果便是懷疑者本身也受到懷疑而消失。對立批判的精神(「創造意義的欲望」)不斷從整體離散出來,終至無所依歸,只能像無廟可棲的散仙那樣,一切存查而轉入意義的嬉遊。這就是所謂「逍遙離散」(ludic dispersal)了。 哈山顯然不滿意這種歷史告終、意義也告終的結局,所以在晚期改採實用主義的多元論,要在局部實況中重建確定性,但同時保存由各種實況的差異所構成的不確定性。這等於是說,後現代精神在到達否定一切的終極困境之後,必須回頭轉向,重尋確定的意義。這裡的問題是,意義分裂、離散的過程是由現代精神的內在規律所推動的,它一旦逆轉而重走聯結、聚合的老路,這內在的動力是不會因為理論家的主觀意志而停留在某一「局部」層次的。從哪裡喪失的確定性,就會從哪裡找回來:既然某些局部實況可以有整體的意義,那麼為什麼不能把社會整體也當成是一種實況,賦與它確定的意義?理論操演固然可以就實況的層級作種種(經驗論的)分辨,但只要理論本身是自律部門的一部分,它所內含的可能性終究會按孔恩式(Kuhnian)科學典範的發展規律,獲得實現。這等於是把後現代反統合、反整體的漂遊觀又重新還原為超然客觀的現代精神。有朝一日,我們又會發現,原來存查院也可以變回監察院。 這種以後現代面目出現的現代精神,在實用主義多元論的立場中已經可以看出端倪。表面上看,實用主義既保全了後現代尊重局部實況的精神,又可避免陷入虛無空洞的反現代的嬉遊,似乎是後現代理論的合理歸宿。其實,實用主義常被認為是一種過度保守的主張,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多元論的前提是: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不同,但可以並存(一個典型的說法是:「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可是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然而多元論既然是以理論的形式出現,這個前提往往會一般化而變成這樣:此狀況的真實與彼狀況的真實可以並存,但不能相同(「我支持你說話的權利,可是不管你怎麼說,我都不贊成你的說法」)。也就是說,多元論者所占的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可以決定各種實況的界限,判斷由其中確定出來的意義是否合法,然而他自己卻是不受任何實況限制的超然旁觀者(只有他才能決定別人有沒有說話的權利)。在哈山討論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時候,這個傾向表現得特別清楚: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在過去的實況中產生出來的,所以不能把自己當成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其實,這是非常形式化的規矩;真正值得考慮的應該是:過去的實況與當前的實況有沒有一些相通的因素,可以為後來者借鏡?馬克思主義者顯然是認為有。那麼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針對事實來討論各種實況之間可不可以相通的問題,而不是跳出實況,斷言所有追求普遍性的理論都是意識形態。這裡哈山的表現多少會令人懷疑,所謂實用主義的立場是否就是要切斷實況與實況之間的連繫,以多元存查的方式達成社會體制的超穩定化? 透過離散與聚合的循環變形,哈山抹除了現代與後現代的差別。然而,如果實用主義就是最後的結果,我們也許應該重新考慮,這套解釋是否有什麼遺漏。我的看法是,在現代精神裡面,文學或其他文化部門具有批判、理議的功能,應該不是問題。問題在:批判而必形成批判部門(監察而必成立監察院),就開啟了批判走向反批判(監察走向存查)的路程。不管是確定性或不確定性,都不可能只存在於某一特定的部門,而是散布在社會整體的各個部分,接受各種現實狀況的制約與決定。文化部門的獨立是現代學術發展過程中的事實,但這並不是說,獨立的結果就必然會產生一個形態確定,負有固定任務,與現實條件完全脫離互動的自律體。哈山既然認為西方文學有一主流,必然是要就文學的內在規律來發展他的思考。結果,社會整體並沒有向文學所提出的對立面理想演變,反而是文學本身(或者說哈山的敘述)不得不按內在規律走入自己的反面。 如果說反本質是後現代的一個特徵的話,那麼這種部門獨立,角色獨立的思考格局恰恰是陷入了文學本質的舊套。但是我們也常聽到 (不限於哈山),後現代就是反這個,反那個,或者是後現代具有三點特徵、五點特徵等等的概括性說法,這一類的「定格畫面」難道不也是有關後現代本質(或內在規律)的,非常確定的描述嗎?這些都是因為形式概括而造成意義必須走入反面的例子。後現代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有「有時反有時不反,才是真反」之類的詭辯,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恐怕由內顯走向外繫,根據實況引入形式、規律之外的決定因素,才會有更具建設性,更實用的結果吧。 第一章 沉默的文學 文學中前衛的觀念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顯出了不合時宜的天真。我們看慣了危機,也失掉了頗為自信的方向感。何去何從?文學掉過頭來反對自己,渴望沉默,留給我們的只是說明憤怒和啟示錄式(outrage and apocalypse)的種種令人不安的通告。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某種前衛的話,那就很可能是想要通過自殺去發現什麼的傾向。這樣,反文學(anti-literature)這一術語就像反物質(anti-matter)一樣成了一種象徵。它不僅象徵了形式的顛倒,而且也象徵了意志和能量的顛倒。那麼,對所有那些以文字為業的人,未來意味著什麼呢?難道竟是無休無止的漂泊和災難嗎? 儘管我不相信語言能夠窮盡精神的各種可能性,然而我卻要承認,災難的來去自有其狡詐的規律。神祕家們總是說,黃泉之路就是出路,事物的終結必將引出新的開端。正如我們今天所說,負面的超越(negative transcendence)也是一種形式的超越。因此文學中的沉默未必預示著精神的死亡。 這裏要談的新文學的要點顯然與過去的文學不同,不管它究竟 「新」在哪裏,我們都無法用過去衡量「前衛」文學的社會標準、歷史標準和審美標準來衡量它。新文學中有一種逃避或者無視傳統的力量,這種力量相當激烈,它摧毀了文學之樹的根基,引出了一種隱喻意義上的巨大沉默。這種力量還沿著它的主幹向上,直達枝葉,綻放出一簇音調混亂嘈雜的花朵。在這許多雜亂的音調中最響亮的是憤怒的呼喊和啟示錄式的調子。亨利.米勒和撒繆爾.貝克特就頑強地唱著這種調子,傳達著沉默的信息。他們的聲調空洞無謂,使用的手法也不再是奇特的比喻。他們是當代想像力的一面鏡子,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那些特別的公設。用一句老話說,他們是當代前衛派的大師。 要談米勒和貝克特需要首先對沉默的成分做些澄清。我想先談談「憤怒」。「難道藝術總是憤怒,或者從本質上說必然是憤怒嗎?」勞倫斯.達雷爾(Laurence Durrell)有一次想到米勒時這樣問道。我們可以同意這樣的說法,即藝術包含著危險甚至顛覆的成分,而無須說一切藝術都是憤怒。現代文學中一個特殊的類型似乎證實了達雷爾的觀點。它處理的人生經驗使他驚愕,那是一種具有形上反叛意義的經驗:如果太陽侮辱了亞哈(Ahab),他也會反擊太陽;伊萬.卡拉馬佐夫(Ivan Karamazov)把生命之券歸還給上帝。這既是一種形上的反叛,也是一種形上的投降,即對虛無的渴望。正如阿爾伯特.卡繆(Albert Camus)講的那樣,心靈的呼喊被它本身的反叛耗盡了。在憤怒中人的本質存在(the very being of man)受到考驗,隨即產生了一種暴力的辯證法,魔鬼般的行動和魔鬼般的反動被壓縮在一個最終變成零的可怕的統一體中。 這種和新文學緊密相關的暴力顯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它預設了達豪(Dachau)和廣島(Hiroshime),當然不限於這兩個地方。認為這種暴力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想法是荒唐的。這種暴力的作用是把人變成物,在它的作用下,人的變形是逐級而降的,往往最終變成貝克特筆下的蟲、巴羅斯(William Burroughs)筆下的蟲人和知覺的滲出物。這種暴力不是時間的,而是空間的,不是歷史的,而是存有論的。它是一幅風景畫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弗里德利克.霍夫曼(Frederick J. Hoffmann)在《致命的不》(The Mortal No)中說,這一暴力的景象說明「無論施暴者還是受害者都已沒有人的味道,二者都是這幅風景畫的部分」。這一把暴力比做風景畫或內在特質的隱喻是我將要討論的暴力定義的一個極端。在百老匯改編上演的米勒作品《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the Tropic books)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幅暴力的風景畫是怎樣形成的。當暴力在貝克特的《終局》(End-game)或《怎麼會是這樣》(How It Is)空空蕩蕩的空間中最後變成死亡時,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暴力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在這些場景之上總是籠罩著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 正是在這一點上,沉默的文學中能夠產生一種相反的動機、一個新的術語。既然憤怒是對虛無(void)的反應,為什麼不可以是對存在的召喚呢?如果這種說法能夠成立,憤怒就會引出相反的動機,那就是啟示。這種轉化明顯地表現在黑人文學中。在這類作品裏傳統的抗議轉變成現代的憤怒,而現代的憤怒又轉變成神的啟示。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為自己一本頗具威脅性的文集題了一個含有啟示錄意味的卷首語:「上帝給挪亞彩虹作標記:今後不再有洪水,可下一次將是烈火。」他還以《下一次是烈火》作為這本文集的標題。勞倫斯(D. H. Lawrence)認為,在那些遭受壓迫的人心目中,含有啟示錄意味的暴力正是對敵人應有的懲罰,甚至千年至福王國在他們看來也是權力而不是愛。就最近其他的文學類型而言,在啟示錄式的隱喻之後往往表現出更為複雜的情緒,隱含著某種近乎全盤否定西方歷史和文明,甚至全盤否定人的本質特徵和人為萬物尺度的傾向。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說:「我要成為一架機器。」不論這是否在開玩笑,他畢竟替貝克特筆下那些肢體殘缺的人、米勒筆下那些貪淫好色的人、巴羅斯筆下那些癮君子說出了他們要說的話。的確,對西方本身的極度厭惡比對其歷史和文明的否定更深刻地動搖著它的基礎。當這股極度厭惡的情緒在狂歡鬧飲式的毀滅中找不到圓滿的歸宿時,就很可能轉向佛教禪宗、帕塔費西學(Pataphysics)或群居雜交。 對自我的極端厭惡是現代啟示錄中介於毀滅衝動和幻想衝動之間的中間環節,也是再生的準備。所以勞倫斯相信,「只要我們和太陽在一起,一切都會慢慢地發生的。」無論太陽多麼遙遠,畢竟在我們的視野之內。惠特曼(Walt Whitman)在某種意義上對我們的心情更有預見性,指出千年至福王國的完滿不在未來,恰恰在永恆的現在: 也沒有比現在更多的青年或老年, 將來也不會有比現在更多的圓滿。 神的啟示就是現在!這個術語(apocalypse)恢復了它的本意,從字面上講,就是向人們揭示祕密和真理,讓幻象穿透一時的迷惘,直達光的中心。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一種非道德的唯信仰(antinomian belief),這種信仰有時可稱作意識的改變(alteration of consciousness),我們可以在阿卜特(Alpert)和李爾瑞(Leary)以迷幻劑產生刺激的實驗中,在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詩歌中、在梅勒(Norman Mailer)對性高潮的賴希式考察中、在諾曼.奧.布朗(Norman O. Brown)的心理—神祕啟示作品中看到這種意識的改變。意識的改變是梅勒畢生的願望,他曾在自己那些啟示錄式的長篇大論中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意識的改變也是貝克特滑稽模仿的目的,從他作品中那些笛卡爾式的獨白中很容易看出這一點。他們倆人的作品都呈現出無言之美的對立狀態。可見啟示並不存在於薩滿教式的迷狂或精靈附身式的恍惚中。正如萊斯利.費德勒(Leslie Fiedler)在《等待終結》(Waiting for the End)中所說:「我們無須開一槍,也無須建構一個三段論式的邏輯體系,只須改變自己的意識就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改變的方式輕而易舉,……」這是一個革命的夢想,旨在結束一切革命或者說一切夢想。 這樣,憤怒和啟示錄就為當代的想像提供了鏡子的形象,這些形象包含了我們經驗中生機勃勃和危機重重的部分,它們正是米勒和貝克特反映截然相反的兩個世界時採用的形象。貝克特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了無生趣的世界,除非發生巨大的變化不能使這個世界復甦。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處於一種幾乎沒有憤怒的狀態。米勒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混亂迷狂的世界,這個世界處於不斷轉變的邊緣上。在這樣的世界裏我們成了啟示錄熱的見證人。這兩個世界的共同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沉默,因為人在恐懼和狂喜的狀態下是講不出話的。 如果說憤怒和啟示錄的極端反應能夠說明新文學的總體面貌,那麼另外一些觀念則有助於說明沉默是新文學的核心。這些觀念中最重要的也許是「荒誕的創造」(absurd creation),這一觀念迫使作者反對甚至蔑視自己的活動。卡繆說:「創造或不創造都不能改變什麼,荒誕的創造者並不獎賞自己的作品,很可能始終拒絕承認它。」這樣,想像力就丟棄了古老的權威,不是在被詛咒詩人的浪漫遐想中,而是在那些把空白頁裝訂成冊的無詞作家的嘲弄中找到了自己的極致。 當作家屈尊把言詞寫在紙上時,他便傾向於把反文學看作單純的行動(pure action)或者無用的遊戲(futile play)。我們知道,藝術是行動的觀點在讓—保爾.沙特(Jean-Paul Sartre)的《什麼是文學?》(What Is Literature?)中獲得了明確的表述。沙特指出,講話就是行動(To speak is to act),我們所命名的每一樣事物都喪失了自身的天真,成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倘若說藝術具有價值,那是因為藝術公開宣稱自己是一種大眾的需求。卡繆(則在《西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頌揚理解生命的知識(savoir-vivre),把它置於獲得行動的能力(savoir-faire)之上。可是他們的這些觀點在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s)中受到了奇特的挑戰。帕洛克不把藝術看作大眾的需要,而是把它看作創造的過程。按照他的看法,這個過程即便不完全是隱私的,也是個性化的。它的價值對它的創造者比接受者更可貴。米勒的觀點與此意外地相似,他認為寫作就是寫自傳,寫自傳就是治療,也就是對自我採取行動的一種方式。他說,「我們應該檢查自己的日記,這樣做不是為了尋找真實,而是把它看作盡力擺脫對真實執迷不悟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做的權利自然屬於記日記的人,但當行動導向外界時也屬於詩人。米勒說:「我不認為那些寫詩(不論是有韻體還是無韻體)的人是詩人,我把那些能夠深刻地改變世界的人稱作詩人。」 可是對貝克特來說,寫作就成了荒唐的遊戲。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對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那個著名論點的滑稽模仿。維特根斯坦這一論點說,語言是一套遊戲,近於原始部落的算術。貝克特的模仿充滿了自怨自哀,顯示了一種反文學的總趨勢。休.克納(Hugh Kenner)對這個問題有精彩的論述,他說:「當今佔主導地位的智性類比不是從生物學和心理學(儘管這是我們正在研究的兩門學科)做出的,而是從一般的數字理論(general number theory)做出的。」這樣,處於封閉領域的藝術就變成了一套排列組合的荒唐遊戲,好像馬洛伊(Molloy)在海邊啜石頭那樣。格奧爾格.施泰納(George Steiner)把這種情形稱作「從語言的撤退」,這樣的遊戲把語言簡縮成了單純的比率(pure ratio)。 十分有趣的是,文學作為遊戲和行動的觀念還產生在另一種富有沉默意味的形式中,它就是文學上的猥褻(literary obscenity)。猥褻這個術語聲名不佳,除了法庭斷案之外很難界定。這裏我用它主要是指那些把猥褻和抗議結合起來的作品。我們不難理解,在一個性遭到壓抑的文化中,抗議完全可能採取帶有猥褻意味的形式,因此,展示這種動機的文學就是一種反叛文學。然而,猥褻是極端簡縮的,它的語言、場所和慣技非常有限。當它背後的怒火冷卻下來之後,猥褻便變成了排列組合的遊戲,可仰仗的詞語寥寥無幾,而行動則更是少得可憐。顯然,這正是我們從薩德(Marquis Sade)的作品獲得的雙重印象:一方面,他的抗議異常強烈,另一方面,他的遊戲竟最終變得麻木。今天許多人都把他看作前衛派的第一人。他的作品表現出奇特的寧靜,作品中的猥褻和不斷出現的暴力窒息了語言。他把色情美學(pornoaesthetics)遺贈給了文學,也把它傳給了海勒和巴羅斯之輩,使他們能夠對性暴力進行滑稽模仿。不過,梅勒筆下的性英雄行為看來仍然太天真,尚難認識到自我滑稽模仿的潛力,而貝克特則對大便排泄的迷戀進行了充分的自我滑稽模仿,同時排斥一切形式的愛。在猥褻中和在滑稽模仿的遊戲中一樣,起制約作用的是反語言(antilan-guage)。梅勒和貝克特在這方面形成鮮明對比,暗示了色情中生殖器和肛門兩種不同的方式。 沉默的文學還以另一種方式成功地否定了文學以時間為特徵的功能,那就是渴求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具體性(impossible concreteness)。這種新的傾向產生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具體音樂(Musique concrete)、從杜象(Marcel Duchamp)到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雜物拼湊畫(collage)、施維特斯(Kurt Schwitters)的環境雕塑(environmental sculpture),以及在施維特斯和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pollinaire)影響下形成的具體詩(concrete poetry)中。這種具體詩是語言和視覺兩種效果雜交的形式,主要依靠字母形成圖畫。此外,在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凶殺》(In Cold Blood)中也可以感覺到那種不甚分明地渴求具體性的傾向。卡波特摒棄想像的魅力,自稱要絕對忠於事實,寫出了他所謂的第一部「非虛構小說」。在歐洲文學中,這種新寫實主義(neoliteralism)有時不是和報導文學聯繫在一起,而是和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聯繫在一起。胡塞爾曾對沙特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這樣不同的人產生過重大影響。他的思想十分難懂,要想加以概括而又不嚴重歪曲它是幾乎不可能的。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說,他的哲學界定了主觀意識的一種純形式,這種意識形式既不是由部分構成,也永遠不會成為經驗的對象,而是通過一系列的「還原」(reductions)被隔離出來,它已經不再是包含著普通人事、感情和感覺的日常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通常接受為自我的東西必須置於「括號」中或者被懸置起來,作為一個經驗的統一體,經過最終「先驗的還原」產生純粹的意識。所以,粗略地說,自我是不可知的,或者像貝克特筆下的反英雄那樣,是不可命名的。 這一結論對小說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因果論、心理分析、象徵關係這些中產階級小說曾一度心安理得地遵循的原則現在開始瓦解了。貝克特的《馬洛伊》可能是用全新的觀念寫的第一部小說,當然,沙特的《惡心》(La Nausee)也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從洛根丁(Roquentin)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對世間萬事萬物都極度冷漠的人,看到事物和語言之間完全脫了節,主觀和客觀之間也完全脫了節。後來,阿爾.羅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出來,反對沙特的泛人類中心主義(pan-anthropcentrism),摒棄了沙特的人道主義,開創了新局面。羅勃—格里耶認為,如果人期望孤獨,拒絕和宇宙交流,如果人證明自己不是斯芬克斯(Sphinx)那個永久之謎的答案,那麼他的命運就既不是悲劇的,也不是荒誕的。他快活地爭辯道:「物就是物,人也只是人。所以我們拒絕和客體的一切同謀關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拒絕一切預先安排好的思想。」按照這樣的觀點,小說家只能是拘泥於字面意思的人,只是給事物命名,或者遊戲於純粹的意象之間。法國薩格特(Nathalie Sarraute)、布托爾(Michel Butor)和羅勃—格里耶就是這樣的小說家,他們的反小說(antinovel)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隱喻和意義、沒有假裝的「內在性」(interiorness),就像新電影(the new cinema)一樣,旨在獲得默片的效果。哈洛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講的好像完全不是文學、視覺藝術:「法國所有的煉金術士(alchemists)追求的都是同一樣東西,即總是通過使語言沉默來獲得新的現實。」 新文學中的沉默還可以通過激進的反諷(radical irony)獲得。這種反諷指所有帶反諷意味的自我否定。克里特人宣稱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謊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廷格里(Jean Tinguely)的機器是另一個例子,這種機器除自我毀滅之外別無用處。換言之,激進的反諷需要的不是一堆東西的雜湊拼貼,而是一片空白的畫布。它的現代淵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紀文學的一些主要人物,特別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夫卡表述的是一種近乎空白和凍結的空間感,而托瑪斯.曼喜歡表達的是一種反諷的調子,這種調子能通過滑稽的自我模仿取消自己,他認為這才是藝術的唯一希望。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說得好:「在《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藝術悲傷地為自己神祕的喪失而哀悼,而在《費利克斯.克魯爾》(Felix Krull)中,藝術則高興地向宇宙警察局報告了自身神祕的喪失。這種傾向還可以更早地溯源到德國浪漫派和法國象徵派那裏。近來,這種激進的反諷也大量出現在詭辯哲學中。海德格所謂的「湮滅的神祕」(mystery of oblivion)的思想、勃朗肖(Maurice Blanchot)關於文學是一種「遺忘」(forgetfulness)形式的觀點都說明反諷在理論上獲得了進展。說得具體一點,梅勒的《一場美國夢》(An American Dream)用坦率而諧謔模仿的手法把小說變成了通俗藝術,事實上否定了小說這種體裁。納塔莉.薩格特的《黃金果》(The Golden Fruits)是一本關於小說的小說,小說中的小說也題為《黃金果》在閱讀的過程中這部小說中的小說漸漸湮滅,從而取消了自己。這種反身的技巧在貝克特的作品中可以說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甚至達到了極致。他最近的一部小說《怎麼會是這樣》(How It Is)實際上講的是「怎麼會不是這樣」(How It Wasn''''''''t)。這樣的手法並非瑣屑無用,因為藝術利用藝術來否定自己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植根於人在意識中將自身既看作主體又看作客體的能力。在人的心靈中有一個阿基米德點,當世界變得忍無可忍時,心靈就會上升到涅槃的境界,或下沉到瘋狂的狀態,或者採用激進的反諷來說明藝術處於窮途末路的情形。因此,在貝克特那裏,文學起勁地毀滅自己;在米勒那裏,文學變幻無常地假裝具有生命。更使人難於辨認的是,激進的反諷往往用假象掩飾對藝術的進攻。通過反諷藝術家向繆斯表示最後的忠誠,同時也褻瀆了她。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情感在貝克特相米勒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最後,文學還力圖通過機會和即興之作獲得沉默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是主要原則。這樣的文學拒絕一切秩序(不論是強加於人的還是人自願接受的),因此也排斥目的性。所以它的形式是無目的的,它的世界是永恆的現在。讀這類作品使我們重新感到原始的質樸和天真,一切錯誤和修正都無關緊要,不再存在。作品中的一切都毫無目的,隨遇而安,彷彿禪宗寺院裏的踏腳石那樣隨處拋置,無所用心。約翰.凱奇(John Cage)的作品證實了我們的這一印象。凱奇既是作曲家也是詩人,他比薩蒂(Erik Satie)更讓公眾震驚。他的作品有極大的隨意性,給人以神聖感。他在《沉默》(Silence)一書中說:「我們的目的是肯定現在這種生活,既不想從混亂中引出秩序,也不想在創造中實現改善,只是要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現在過這樣的生活,一旦人們的心靈和欲望離開了它,讓它按自己的意願行動,它就會變得非常美好。」在米勒的作品中、金斯堡的詩歌中、克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中、塞林奈(J. D. Salinger)後期的短篇之作中都可以看出這種無目的性和隨意性。但與凱奇不同的是,這些作家在把自己的精神生活輸入文學實踐時卻顯出了膚淺。例如,米勒雖然很喜歡「道」和彌拉惹巴(Milarepa),卻總想做出一副喋喋不休地敘事的姿態。他作品中那些看來隨意的拼湊雖然不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卻也是經過處理的。多年以前,達達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幾乎要瓦解一切文學形式,可他們缺乏良好的精神素質。我們今天的一些隨意性作家像雷蒙.奎諾(Raymond Queneau)、馬克.薩波塔(Marc Saporta)和威廉.巴羅斯之輩也是如此。在《無數的詩》(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ems)中,奎諾建造了一架「詩歌機器」,十頁十四行詩相互搭接,每一首的每一句都可以和其餘的詩行形成種種組合,這樣,要想「讀」完這些詩就得用兩億年。在《第一號》(Number 1)中,薩波塔要讀者每次讀他這些小說時以洗牌的方式創造出自己的作品來。這種「洗牌式小說」(shuffle novel)顯然是他的一種策略,它提示在文學經驗中機會是一個合法的成分。巴羅斯相信講話就是撒謊,因此力圖通過「布利昂.吉辛的剪碎法」(The Cut Up Method of Brion Gysin)來逃避虛假,這樣就自然回到了達達主義者特利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的滑稽伎倆上。巴羅斯解釋說: 方法是簡單的:從你自已的作品或者從活著的,已故的作家的任何作品中取出一頁左右的篇幅,可以是書面的也可以是口頭的,然後用剪刀或彈簧折刀將其隨心所欲地剪成小片,在反覆的觀察中把它們重新安排,寫出結果。 剪碎法的應用可以是無限的,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古老的文字把你侷限在古老的框框裡。用剪刀剪出你自己的路子來。可以剪紙剪電影剪磁帶。想剪什麼就剪什麼,直至剪碎城市。 達達主義的雜湊拼貼、佛教禪宗、或者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遊戲理論可以同樣有效地使人們擺脫傳統的語言文字習慣。巴羅斯和貝克特有一些共同之處,他們都使用了減數機(subtracting machine)起落無常,極不流暢的節律。這種機器的目的無非是給語言動手術,從而減掉一切意義。 顯而易見,處在反文學核心的沉默是大聲喧嘩的、多種多樣的。不論它來自憤怒還是來自啟示,不論它出於單純行動還是單純遊戲的文學觀念,不論它表現為具體物品、還是空白頁或者雜亂拼湊,最終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認為重要的是這樣一點,沉默是文學對自己採取的一種新態度,是說明這種新態度的一個隱喻。這種新態度對文學傳統論述方式的特別權力和優越性提出疑問,對現代文明的許多公設發出挑戰。 從總體上看,這種新態度並沒有對英美批評家產生足夠的影響,這一點頗使人迷憫。英國人看問題明智、務實,而美國人則長期陷在那個費力的形式主義中,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他們對這種新態度冷漠的原因。此外,在英美兩國,反文學的思潮往往使那些人文主義思想相當牢固的批評家們不滿,也使那些篤信某種現實主義觀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反感。 法國批評家很可能也像別國的批評家那樣盲目教條或狹隘偏執,但對反文學的思潮卻表現出例外的熱情。沙特在《什麼是文學?》中用較多的篇幅討論了本世紀初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語言危機。十年之後,他在為薩格特的《無名氏畫像》所寫的導言中說:「就其生動性和全部否定性而言,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一部反小說。」這樣就為本世紀中期的批評詞彙庫中增添了一個新術語(anti-roman)。莫里斯.勃朗肖在《未來的書》(Le Livre a venir)中把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看作沉默傳統中的始作俑者,說他「熱衷於寫反寫作(contre l''''''''ecriture)的東西」。他認為文學正在接近「沒有話語的時代」(l''''''''ere sans parole),像貝克特和米勒的某些作品就只能理解為一系列連續不斷的聲音。所以按照勃朗肖的看法,文學正在接近自己的本質,那就是消失。羅蘭.巴爾特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的《寫作的零度》(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主題就是缺失(absence)。他認為「現代性始於對不可能存在的文學(litterature impossible)的探索。」,而探索的結果便是奧菲斯的夢:「出現一個沒有文學的作者」(unecrivain sans litterature)。克洛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似乎是第一個把米勒和貝克特放到一起來討論的批評家,他在《新文學》(The New Literature)中說:「經過韓波(Arthur Rimbaud)的沉默、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的空白詩頁、阿爾托(Antonin Artaud)無言的呼喊之後,非文學(aliterature)終於消解在喬伊斯(James Joyce)的頭韻中。……而對貝克特來說,所有的詞說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可見,儘管法國人頭腦也很清醒,但卻並沒有對文學的沉默提出責難。 但我還是懷疑僅有思想的清晰是否足以實現批評的偉大目標。我們越來越感到批評應該在澄清和解釋之外做更多的工作,應該具有感官和精神的智慧。我們要求批評像文學一樣使它自身處於危險中,從而證實我們的處境。我們甚至希望它能承受啟示的重任。這一希望引導我們提出這樣的假想,它應該成為啟示災變的工具,從而使我們產生應有的警覺。至少它應該對啟示錄的隱喻抱有同情心,以便考驗反文學的直覺。萊斯利.費德勒的《新的變異》是美國批評中討論批評重任的一篇珍文,此文說明他能充分理解文學想像和沉默、猥褻、瘋狂、甚至近於神祕恍惚的後性狀態(post-sexual state)結合在一起時產生的複雜性。他懂得,對我們這個時代至關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意識,文學首先孕育一個可能出現的未來,……然後以歡樂和可怕的預言裝備那個未來,這樣,就使我們所有的人為未來的生活做好準備。」 反文學可以導向未來,然而批評的心靈仍要求歷史的保證。沉默的文學會回憶起第一個歌手奧菲斯被肢解的情形嗎?會顛倒那個把文字轉變成血肉的聖經式奇跡嗎?難道人類在經過漫長的史前期之後必須屈從於一個無言的事嗎?完全相反,新文學可以是極端的,它的夢可以是啟示錄式的、憤怒的。它是為生活而生的,而生活,我們知道,有時要經受暴力和矛盾。 神話中有一種說法,說奧菲斯被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狂友們(Machads)根據她的命令撕成了碎片。還有一種說法,說他是被她們在無法控制的嫉妒中殺死的,因為自從他的妻子歐律狄克(Eurydice)死後,他就不近女色而寧願與青年男子作伴,故而引起了那些狂友們的嫉恨。不管是哪一種說法,有一點是共同的:作為一個超常的創造者,他是酒神原則和日神精神衝突的犧牲品。前者以酒神的狂友們為代表,而後者則是他作為一個詩人崇拜的對象。奧菲斯被肢解之後,他的頭依舊在歌唱。在他的肢體被謬斯們埋葬的地方,夜鶯的歌比世上任何地方的歌都甜美。奧菲斯的神話可以成為某些時期藝術家的寓言。由於文明總是要對酒神精神加以壓制,因此酒神精神在一些時期往往威脅要進行凶猛的報復。這樣,在這個報復的過程中,精力就可能壓倒秩序,語言就可能變成狂嚎、母雞的叫聲和可怕的沉默。形式也就可能像可憐的奧菲斯那樣被無情地肢解。然而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難道詩人的頭不是必然會像那狂暴的日子在色雷斯(Thrace)山中那樣被砍下以便繼續他的歌唱嗎?讓我把問題提得更直接些:難道生活不是必然會定期地壓制藝術以便保證人的健康和生存嗎?難道語言不是必然會渴望寧靜嗎? 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例證,早先就有過關於沉寂和解體的警告。羅伯特.馬丁.亞當斯(Robert martin Adams)在《不諧的旋律》(Strains of Discord)中恰當地找到了一種結構,認為它是時下反形式(antiform)的前身。他說:「開放的形式」(open form)是一種有意義的結構,它「包含一個主要的,不可解決的衝突,旨在展示這種不可解決性。……在它的左邊,一條不明確的、定量的線把它和無形式以及不確定性(反常的或一般的)分割開;在它的右邊,一條同樣不明確的,定量的線把它和雖然含有開放成分但卻仍是完好的封閉形式分割開。」從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得到啟示的那些嚴肅的類型學家可能希望說明,正因為文學似乎是從神話模式發展到反諷模式的,所以文學形式似乎是從封閉發展到開放,然後再發展到反形式的。當我們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酒神的伴侶》(The Bacchae)對照閱讀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閉形式和開放形式之間的差別。亞當斯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他認為《伊底帕斯王》力圖解決衝突,使觀眾產生一種局部寧靜的心態,但《酒神的伴侶》卻給觀眾留下了一種無法緩解的痛苦。作為一個封閉的形式,《伊底帕斯王》表達了一種保守的、宗教的世界觀和集體經驗,而作為一個開放的形式,《酒神的伴侶》卻表達了激進的、懷疑的世界觀和個人經驗。如果按照這一圖式大膽推論,我們不妨說,貝克特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是一種反形式,暗含著一種反諷的、虛無主義的世界觀和一種完全隱私的經驗。 不過,我們不必拘泥於嚴格的類型學,這樣就可以看到,從《酒神的伴侶》到《等待果陀》之間,西方文學中有大量的作品表現出不斷增長的斷裂感和扭曲變形能力。僅以戲劇為例,我們就可以提出如下序列: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畢希納(Buechner)的《沃伊采克》(Woyzeck)、梅特林克(Maetelinck)的《青鳥》(Blue Bird)、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夢劇》(A Dream Play)、加里(Alfred Jarry)的《于比王》(Ubu Roi)、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熱奈(Jean Genet)的《黑人》(The Blacks)、尤涅斯柯(Eugene Ionesco)的《殺人者》(The Killer)。看來戲劇形式似乎是從不可解決的矛盾走向象徵主義的逃避,然後從象徵主義的逃避走向超現實主義或表現主義的扭曲,最後從這種扭曲走向荒誕。儘管歷史上有過無可辯駁的例外,這種從形式向反形式的發展是西方的主流,它不僅表現在戲劇中,而且表現在藝術的整體中。 也許這樣講大抵是公正的:風格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先後出現標誌了形式運動的三個階段。風格主義是文藝復興的風格在形式上的消解,正如韋利.賽弗(Wylie Sypher)在《文藝復興風格的四個階段》(Four Stages of Renaissance Style)中所說,是張力和遲疑不決的一個標記。在風格主義藝術中「心理效果脫離了結構上的邏輯」。對我們一般所說的開放形式,賽弗的看法是: 在風格主義精心設計的技巧後面往往有一種個人的不安、一種激發出形式和詞藻的複雜心理。當我們考察繪畫、建築和詩歌裡風格主義結構中的張力時,我們就必然會清醒地意識到風格主義氣質中這種禍害或者說流沙。風格主義是技巧的實驗。它採用的技巧有:破壞比例和打亂均衡、Z字形和螺旋形的穿梭運動、旋渦般或狹巷般的空間、傾斜的或流動的視點、奇特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只能產生近似而不是確定效果的透視法。 這不正是我們閱讀莎士比亞的後期劇作、詹姆斯一世時期的戲劇、玄學派(或譯形上派)詩歌時的感覺嗎?不正是我們觀賞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埃爾.格列柯(El Greco)的繪畫時的感覺嗎? 浪漫主義者由於在朦朧的心緒中總是渴望著無限,因而進一步走向了不穩定的文學形式。《浮上德》正站在這一時期的門檻上,它混合著來自異教和基督教的雙重影響,在結構和主題兩方面變成了對生活中憤怒的矛盾的請求——只有歌德那光輝閃爍的天才方能把這樣的戲置於藝術的控制之下。這群陰暗的、浪漫主義的英雄們——浮士德、恩底米翁(Endymion)、阿拉斯托(Alastor)、唐璜(Don Juan)、于連.索黑爾(Julien Sorel)、曼弗雷德(Manfred)、阿克塞爾(Axel)——總是威脅要衝出束縛他們的樊籠,高傲地反對他們的創造者。自我、夢和無意識都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強烈地表現出來。諾瓦利斯(Neval)和奈瓦爾(Nerval)、霍夫曼(Hoffmann)和愛倫坡(Poe)、克萊斯特(Kleist)和畢希納、柯勒律治(Coleridge)和濟慈(Keats)把語言引入靈魂的暗夜之中,或者說培植出聲名不佳的浪漫主義反諷,從而在每一個表述中表達自己的反面。在另一些情況下浪漫主義堅持乖戾反常的性情,從而使自己失去了和諧和穩定的可能性。它探索薩德主義(性虐待狂)、惡魔主義(對惡魔的信仰)、神祕主義(cabalism)、對屍體的性迷戀(necrophilia)、吸血主義(vampirsm)和變狼狂症(lycanthropy),在毫無人性可言的情況下探索人的定義。難怪歌德認為浪漫主義是病態的形式,雨果(Victor Hugo)要把它看作古怪的東西。當然,我很清楚,這裏強調的是浪漫主義運動中黑暗的衝動,然而現代文學正是從這種衝動中獲得了動力,也正是這種衝動(倘若你願意,也可以稱這種衝動為巨痛)幫助摧毀了古典的文學形式。馬里奧.普拉茲(Mario Praz)在《浪漫主義的巨痛》(The Romantic Agony)中說:「浪漫主義的本質在於無法言表。.…‥浪漫主義把藝術家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而藝術家卻不能賦予自己的夢一種物質形式——詩人面對著永久的空白詩頁欣喜若狂;音樂家傾聽著自己心靈中的音樂會而無意把它們變成樂譜。把具體的表述看作墮落和污染正是浪漫主義的態度。」可見,浪漫主義是沉默的源頭,是無言文學(aliterature without words)的源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那種鄙視一切而只願意以最原始、最神祕的方式使用語言的文學的源頭。法國象徵主義者是現代運動的直接祖先,他們為現代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典範。馬拉美的十四行詩設計了自我消滅的句法:韓波的《靈光篇》(Illuminations)打亂了語言的指示作用,意在使官感發生紊亂。勞特萊蒙(Lautreamont)的《馬爾多羅之歌》(Maldoror)為超現實主義開闢了道路。諾曼.奧.布朗說得好,在後期浪漫主義中,酒神重新進入了文學的意識。可以更加肯定的是,浪漫主義從語言的二重撤退是很明顯的。這撤退發生在馬拉美反諷的、自我取消的方式中,也發生在韓波不加區別的、超現實主義的方式中。在前一種情況下,語言渴望走向虛無,在後一種情況下,語言渴望囊括一切。前一個的關聯靠的是「數」,後一個的關聯靠的是「行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文學恰如勃朗肖所說正在走向自身的消失,也許馬拉美、卡夫卡和貝克特正屬於這一類型,在後一種情況下,文學恰如加斯東.巴歇拉(Gaston Bachelard)所說正在把自我重新組合成「熱烈的生活」(la vie ardente),也許韓波、勞特萊蒙、勞倫斯和米勒的部分正屬於這一類型。這兩種類型都在恐怖中找到了自己的源頭(所以兩者都包含在一位更早的前衛派作家薩德的思想裏,薩德懂得,憤怒和祈禱最接近文學的中心。),都最後走向沉默,切斷了語言和現實之間的一切關係。 在現代主義中,有組織的混亂(organized chaos)是制約一切的因素,正如葉慈(W. B. Yeats)在一首充滿啟示錄精神的詩中所說的那樣: 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處放縱著混亂無序, 血色暗淡的潮流奔突洶湧。 在有限的篇幅中要把我們這個世紀主要作品中表達的解體與重新組合的情形說得一清二楚是不可能的。喬伊斯曾是少數相信語言的作家之一,他在世時相信語言可以取代世界,在《芬尼根們的守靈》中卻以一個獨眼巨人的雙關語說明語言的終結。卡夫卡冷靜地確立了文學能夠具有的可怕的不確定性,說明了愛或恐怖最終將阻止語言發揮任何作用。未來主義以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為代表轉向另一個極端,文學成了一個想像的強盜,用鎢和斧劫掠城市。馬里內蒂假裝站在世紀的最前沿,向空氣發表演講。對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現在尚難做出全面評價。這兩個運動把生活和藝術中所有虔誠的東西徹底翻了個兒。它們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每一位作家必須面對的挑戰。因為雖然他們用我們通常不用的語言講話,但他們的目的仍然是為了生活和進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開始發表作品的作家們從總體上看不那麼雄心勃勃,可劉易斯(R. W. B. Lewis)還是看出了他們和前代作家之間的區別。他指出,馬侯(Andre Malraux),卡繆、葛拉姆.葛林(Graham Greene)這一代作家和那些把審美經驗看待至高無上的前代作家是完全不同的。他在《流浪的聖哲》(The Picaresque Saint)中說,這些年輕一代作家們的「主要經驗是發現作為一個作家的意義和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他的結論是「批評在審視這個世界時將會陷入更激進的思考中,思考生與死,思考人充滿渴望的、罪惡的本質。」至於我們當代的文學,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講得很中肯,他說比起早先的各式現代主義文學來,我們的文學更「分崩離析」,對奧菲斯的肢解表現出更大的熱情。文學走向反文學,並在此過程中創造了愈來愈瘋狂、愈來愈混亂的形式:新流浪漢小說(neopicaresque)、黑色滑稽作品(black burlesque)、怪誕作品(grotesque)、哥德式小說(gothic)、噩夢式的科幻小說(nightmarish science fiction),不一而足。最後,混雜在沉默中的便是表達憤怒和啟示的種種反形式。 歷史畢竟不能保證給人任何慰藉。安東尼.阿爾托在1938年出版了一本書,後來被譯作《戲劇及其替身》(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他在這本書中說道:「如果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一個該死的、地獄般的東西,那就是我們對形式高超的戲弄,這種戲弄比犧牲者被綁在火刑柱上焚燒,通過火焰傳達信號的把戲更令人痛恨。」奧菲斯不僅被肢解了,而且他的四肢被燒灼出白熱的光。歷史把我們帶到一個時刻的門檻上,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棘手的問題。為什麼對這個文明的厭惡竟把文學逼到這樣一個極端的地步,使它陷入如此可怕的沉默呢? 在對我們的弊病作出全面的診斷之前,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只能是間接的。也許線索仍舊在奧菲斯的神話中,在阿波羅(日神)和狄奧尼索斯(酒神)永無休止的鬥爭中。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對此提出了頗有說服力的見解。他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說明,社會建立在本能壓抑的基礎之上。對這一點我們一直有同感。但我們並未能時時意識到的是,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棄絕行動都為進一步的棄絕開創了道路。不僅如此,佛洛依德還爭辯說,文明最核心的動力「要求越來越多的壓抑」,這一過程所付的心理稅是多方面的,它的含義對文學至關重要。諾曼.奧.布朗在他那本頗具影響的著作《生對死的抗拒》(Life Against Death)中從佛洛依德結束的地方起步,提出一切崇高必然意味著對生命本能某種程度的否定。他的結論是:「崇高裏否定的力量鮮明地表現在(語言、科學、宗教和藝術中的)象徵和抽象不可分離的關係上。所謂抽象,正像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告訴我們的,是對經驗的生命器官也即一般生命體的否定。……」那麼,這裏的邏輯——我不知道它是否像布朗和佛洛依德表達的那樣無情——便是:壓抑產生文明,文明產生更多的壓抑,更多的壓抑產生抽象,抽象產生死亡。我們現在正在沿著一條純理智的道路前進,弗蘭采(Frenczi)把這種純理智看作一條瘋狂的原則。那麼,對人類還有任何拯救的辦法嗎?布朗提出了下面的想法: 人的本我(ego)必須面對酒神精神的現實,因此需要做大量自我改造的工作。尼采說得好,日神精神保存自我意識,而酒神精神毀滅自我意識。只要本我的結構是日神的,酒神體驗就只有以本我的解體為代價才能獲得。這種爭端也不可能以「綜合」日神式的本我和酒神式的本我加以解決,因此,已故的尼采竭力鼓吹酒神精神。……而建構酒神式的本我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有跡象表明,這些工作正在進行。假如我們能看清酒神式的女巫在現代歷史中釀成的種種變亂——薩德的性和希特勒的政治——我們也就能夠看清在浪漫主義的反動中酒神精神進入意識的情形。 對新佛洛依德主義者來說,問題是壓抑和抽象,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建立酒神式的本我。他們認為語言最終變成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謂的「身體的自然言語」(the natural speech of the body)。 這裏布朗對尼采的引述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尼采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理智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他既是佛洛依德主義者的祖先,也是存在主義者的祖先。他還是這兩個運動之間的一個活的中介。他對西方文明的分析類似佛洛依德的,也許更有說服力。在他看來,現代世界罪惡的根源不僅來自對本能的壓抑,而且來自人有意識地追求意義的虛無主義。在對十九世紀做了深層的考察之後,他宣稱上帝已經死亡,同時提出現代人的危機是價值危機。「為什麼虛無主義會到來?」在《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書中他提出了這一問題,他的回答是,「因為虛無主義代表了我們最大的價值和理想的邏輯歸宿,在我們能夠看出這些『價值』究竟有什麼樣的價值之前,我們必須體驗虛無主義。在某些時候我們需要新的價值。」尼采像當代存在主義者一樣,認為根本的問題顯然是一個意義的問題。(但與大多數存在主義者不同,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認為通過超人豐富的生活經驗可以解決問題。)按照這樣的觀點,語言的理想變成了行動、姿勢,因為意義的創建不僅是一個語言過程,更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過程。有一位名叫尼古拉.貝加耶夫(Nikolai Berdyaev)的基督徒則對這個問題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釋,「歷史內在的啟示表明:歷史上的上帝之國即意義是不能實現的。」但我們發現,這一問題依然是一個意義的問題。 世俗主義(secularism)、怠惰(acedia)、犯罪和虛無主義可能只是在深層失去意義的一些象徵。人正在失去自己內心的空間,就像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所說的那樣,人獨特的世界已被高度擠壓,難怪傳統上曾是人們在公私場合表情達意最大倉庫的語言也大為貶值。我們這個時代的預言家和烏托邦主義者也未能提出贖回語言價值的辦法。他們把崇高在未來的作用縮減到最小,也就把語言的作用縮減到最小。人類中將會出現的酒神或超人並不是那種健談的生物,因此,現代對語言表述的反叛說到底是對權威和抽象的反叛:日神主辦的文明已經變成了極權的文明,他給人類提供的賴以生存的工具已變成了以抽象為燃料的機器。因而無意義(meaninglessness)便是抽象的相關物。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文學中對語言的反叛反映了但也滑稽地模仿了技術統治中從語言的撤退。這一點正是格奧爾格.施泰納在《從語言撤退》(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中有所忽略之處。當然從其他方面說此文還是重要的。他說: 十七世紀之前,語言幾乎覆蓋了經驗和現實的所有領域,可今天它的範圍變得狹窄了,它不再是表述行動、思想和情感的主要工具。大片的意義和實踐領域屬於數學、符號邏輯、化學方程式或電子關係式等非語言範圍。還有一些意義和實踐的領域則屬於非具象藝術(non-objective art)、具體音樂等亞語言(sub-language)或反語言的範圍。語言的世界已經萎縮了。 然而,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弊端歸咎於上帝的死亡或技術,那樣就過於簡單了。包括阿爾蒂采(Charles J. Altizer)、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凡.布倫(Paul M. Van Buren)在內的更年輕的神學家把上帝的死亡看作文化肯定和精神肯定的一個挑戰性事件。一些搞技術的預言家像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和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 Fuller)等則從「地球村」(global village)看到了神奇的可能性,認為地球已經完全處在新科學和新技術的控制下。但即使麥克魯漢也認識到,在從印刷語言的視覺文化轉入電子技術的「總體」文化這一過渡時期中,我們必須面對可怕的危險。他在《古騰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中這樣說:「恐怖是任何口語社會(oral society)的正常狀態,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件事物與每一件事物之間無時不相互影響。」同時,「我們最普通、最一般的態度好像突然扭曲成古怪的、荒誕的形狀,熟悉的體制和關係好像突然變得恐怖邪惡起來。」不論沉默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它採用什麼樣的形式,它已經成了文學的一種態度,也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事實。 ● < TOP>
作者: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著;沈志明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简介:普鲁斯特是整个20世纪开宗立派、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寻找失去的时间》卷帙浩繁,是整个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全书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可以说是在一部主要小说上派生着许多独立成篇的其他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交织着好几个主题曲的巨大交响乐。本书基本保留了7卷本全本的精华所在,一册在手即可初尝这部巨著的风味,是为“精华本”。
作者: (荷) 韩良忆著
简介: 所属分类:旅游地图 > 旅游随笔 > 《地址:威尼斯》是韩良忆继《在欧洲?逛市集》之后第二本“居游时代”系列图书。 韩良忆以“做一阵子威尼斯本地人”的简单纯粹心情,深入威尼斯大街小巷,寻找并介绍本地人才会吃喝的饮食,本地人才会去的酒馆、餐馆、市集等,而且传授了很多“不当冤大头”的私人秘笈。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韩良忆对威尼斯的历史和文化也有生动精彩的见解,并推荐了很多地道又实用的威尼斯食谱。 作者完全摒弃走马观花的套路,不求全面详尽,而求亲切真实,以非常个人化的角度娓娓讲述,加上豪爽幽默的性格,使得全书精彩不断,读者随着她的叙述仿佛有亲历威尼斯之感。 自序 威尼斯:梦的地址 居游威尼斯的梦想 01 住在天堂威尼斯 “我到威尼斯时,发觉我的梦已经变成我的地址了。 ”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02 享受午后阳光下的广场 威尼斯的大小广场无数,可嬉戏,可闲坐,或是猜猜看谁才是真正的威尼斯人。 03 威尼斯常客其乐无穷 乘着贡多拉横越大运河、到佛罗里安喝杯咖啡、到街坊小咖啡馆当个常客……住在威尼斯的乐趣实在太多了! 04感觉威尼斯的古老灵魂 一艘贡多拉从远远的一头,缓缓向小桥划来,乘着粼粼波光,“威尼斯,真美! ” 05 航向潟湖 遍洒大街小巷的艳丽色彩,让布拉诺小岛有种明快而欢愉的气氛,令人眼前一亮,心情也更轻松。 06 威尼斯日常涂鸦 推开遮阳板,让威尼斯的一天流泻进来,教堂的钟声、维瓦尔第的奏鸣曲……威尼斯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居游威尼斯的美食 07 一口吃下威尼斯历史 我在威尼斯发觉了意大利饮食之美,一顿简单的午餐,仿佛敞开了一扇门,开启了我对意大利菜的偏好。 08 没逛过酒馆,没到过威尼斯? 炙热阳光晒不进的小酒馆,酒意渐渐升起,阴凉空气中盈满笑语,异乡的旅人也变得恍惚起来…… 09 威尼斯最风行的鸡尾酒 细致的汽泡加上粉嫩的色泽,美得犹如一场粉红色的梦幻,酒入喉的那一刻,生命真如一袭华美的袍子。 10 威尼斯餐馆熟客指南 想拥有那种美美地吃了一顿饭之后的陶醉表情,享受用餐的愉悦,只有选对了餐馆,才能真正达成喔。 11 食材采买血拼去 意大利老板习惯一对一慢慢招呼客人。趁机会打量一下店里的新鲜货,体验意大利式的悠闲生活吧。 12 我的威尼斯厨房 用威尼斯的新鲜食材做一顿饭,居游威尼斯的住客时光,才真正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附录 良忆推荐本地美食对照表 威尼斯字汇不一样 已经有太多的人写过太多的威尼斯。而良忆的《地址:威尼斯》即不是信息全面的旅游手册,也不是感慨良多的文化散文,她抱着“做一阵子本地人”的简单纯粹心情“居游”威尼斯,十天半月,并不奢侈。景点变得不再重要——也许从来不曾重要,我们可以就这样随着良忆游走,吃小馆子,广场闲坐,市集买菜,恍惚在威尼斯的氤氲里。即贴近最原味的异乡生活,又游离在日常之外——这本才是旅行的意义。 08没逛过酒馆,没到过威尼斯? 炙热阳光晒不进的小酒馆,酒意渐渐升起,阴凉空气中盈满笑语,异乡的旅人也变得恍惚起来…… 爱上威尼斯的传统酒馆 “到威尼斯而不逛一逛传统的小酒馆,简直就没到过威尼斯! ”里欧如是宣称。 里欧是我采访影展时认识的意大利朋友,他的老家在距离威尼斯六十多公里的小镇,不过大学是在威尼斯读的,毕业后也在水都工作,如今也算半个威尼斯人了。 “逛酒馆在威尼斯可是已流传数百年的传统, ”里欧解释说,“威尼斯人一般并不会一天到晚都在外头用餐,太贵了,顶多一两周上一次馆子,可是到小酒馆里喝杯酒,吃点小菜,花不了多少钱,所以有不少人仍保有三不五时就到酒馆小酌一杯的习惯,因此你在酒馆时碰到本地人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能看到威尼斯日常生活的一隅。 ” 听他这一讲,我还能不去逛酒馆吗?在二度造访水都时,特地请里欧带路,两人一逛就是三家,不停地吃吃喝喝,直到微醺。 从此,我爱上了威尼斯的传统酒馆,后来再赴威尼斯时,不必麻烦里欧,自个儿去逛,只是节制一点,小菜多吃点,酒少喝点,免得一不小心喝醉了,怎么摸回旅馆? 婚后和约柏头一回结伴造访威尼斯,当然要和另一口子分享逛酒馆的乐趣。这一逛,他也逛上了瘾。 威尼斯的传统小酒馆叫做 bacaro或osteria(复数形式分别为 bacari与osterie),介乎酒吧和 trattoria(小馆)之间,有点像是西班牙的 tapas bar,不同处在于, tapas bar既供应凉菜,也有热食,既是可以喝酒吃小菜的酒吧,也是大伙可以结伴游逛的社交场所,所以酒吧里头常附有座位。 威尼斯的小酒馆则不然,传统上根本不设桌椅,也不供应热食正餐,反正本地客人一本威尼斯商人的务实作风,通常没有在酒馆里一待个把钟点的习惯,而是在办完事或下班回家的路上,拐过来喝一杯普罗塞克( prosecco)汽泡酒,吃两口小菜,吃喝完了和酒保及酒馆里其他常客聊个两句,便打道回府,所以用不着坐下,站着就行了。 一直到现在,仍有小酒馆恪守传统,只供立饮立食,仅卖酒和凉菜小吃,而且到晚上八点多就打烊,摆明不做晚餐的生意。只不过,晚近以来,这样老派的酒馆渐渐地少了,现实使然,许多业者为了配合游客需要,也备有桌椅供客人小歇,并卖起简便的面食和主菜。 典型的传统酒馆一进门就是木头柜台,台上的玻璃橱柜里摆了一盘盘 cicheti(另一拼法为 ciccheti),也就是下酒小菜,有洋葱醋渍沙丁鱼、水煮蛋、肉丸( polpette di carne)、火腿腊肠、奶酪,以及意大利文叫 panini的夹馅面包等,琳琅满目,每一份都只合两三口,重质不重量,不求挡饥,只为解馋。 柜台后面的酒架上,排排站着或躺着一瓶瓶的葡萄酒或烈酒,酒架一侧往往有面黑板或告示海报,手写着今日供应之各款可供单杯点用的葡萄美酒,酒名后面的数字就是单杯酒的金额。 来喝一杯“影子”吧 到小酒馆,自然要喝点酒才像话。喝一杯,威尼斯人称之为 ombra,字面上的意思为“影子”。据说在古早古早以前,圣马可广场的钟塔底下聚集着推车卖酒的小贩,每到日头炎炎的午后时分,酒贩们往往随着塔影的移动而变换位置,以便摊车时时得到庇荫,因此劳动大众午休时刻要是想喝杯酒歇息一下,就会说,“我去钟塔乘凉了”,ombra就这样成了喝杯小酒的代名词。 不过,我曾在书上读到另一种说法: ombra和圣马可广场的酒贩无关,其实指的是“如影子一般分量的酒”,意即少量的酒。这似也言之有理,因为 ombra酒杯的尺寸的确较小。我好几回在不同的小酒馆,向掌柜表示要 “un’ombra bianca(rossa)”(一杯白酒 [或红酒 ]),结果酒都盛在比普通葡萄酒杯小一半的袖珍杯里,大约三四口就可饮尽。 还有几次,我改用一般的说法,说要 “un bicchiere”(译成英文就是 a glass),店家递给我的,却是容量较大的一杯酒,不知是各家酒馆习惯不同呢,还是 ombra就是有别于 bicchiere。 大杯也好,小杯也好,用上面这几句话点来的酒,都是所谓的 vino della casa,也就是店家例牌酒,口味较大众化,价钱往往最便宜。有时店家会问你:“哪一种? ”因为光是例牌酒就有好几样选择,拿白酒来说,可能就有 pinot grigio、pinot bianco、soave和tocai等,多半是威尼斯附近产区的酒。 从例牌酒的好坏,可以评量店家酒窖的水平,如果例牌酒的质量超乎一般的好,那这家酒馆可能是特别注重酒的质量的优良店家,这时不妨升级试点其他单价较高的酒,通常也不会令人失望,有时更给人惊喜。这种小酒馆对食物也比较用心,小菜往往好吃。 倘若酒馆的小菜不错,但例牌酒水平就仅仅差强人意,还算过得去,那就多吃点菜,少喝点酒吧。如果酒不行,菜也马马虎虎,干脆列为拒绝往来户,以后不再光顾,何必再上门破坏自己的胃口呢?威尼斯的小酒馆多得很,里亚托市场附近尤其密集,换一家试试看得了。 我和约柏在两次居游期间,有好几回午餐刻意不上馆子正正经经吃顿饭,而去逛酒馆,像小鸟啄食似的,这里埋首尝个两口,再跃到别处又吃上两口。最夸张的一次,早上十点半就开始 in giro per osterie(逛酒馆),逛到下午三点多才罢休。当然啦,我们并不是一连五个钟头都在吃喝,在酒馆与酒馆之间的路上,还是难掩游客本色,不时停下来歇脚休息一下,顺便拍几张风景照片。 典型的小酒馆巡游 我们典型的酒馆之旅是这样的:将近正午时,夫妇俩来到一家 osteria,并不就座,而学本地顾客,端着一杯普罗塞克,斜靠着沿墙而设、权充桌面的长条木架,吃两样 ciccheti,当做“开胃菜”,接着在附近转悠转悠,晃个二三十分钟,等到又有点饥饿感了,再换家酒馆吃“主菜”。这家倘若设有简单的座位,就坐下来,喝个两杯,吃上两三样小菜或 panini。倘若没座位,立食也无妨。 佳酿美点享用完毕,我们常已半饱,决定转移阵地,散个长长的步到另一区,再接再厉,继续吃喝。我的酒量不如约柏好,到了第三家,就只能喝小不点的 ombra,或干脆改喝 fragolino,这是种微含汽泡的甜酒,有红也有白,带着草莓香,却是葡萄酿制的,它的酒精含量比一般葡萄酒低,适合当饮料或饭后酒。 我感觉得到体内的酒意慢慢升起,索性倚靠在柜台边。时值午后,日头正烈,炙热的阳光却晒不进位于窄径一侧的小酒馆,屋里灯光昏黄,阴凉的空气中盈满了窸窣的笑语,有一对中年男女聊得正高兴,如歌一般的意大利语一波波地传送至我的耳畔,我仿佛听懂了几个单字,其实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这样朦胧暧昧的瞬间,很容易就使得异乡的旅人蓦地恍惚起来。 坐落在鱼市附近的这家小酒馆,开业已经五百多年了,柜台两端的脸孔不知已换过多少世代。过去,酒馆的主人在这儿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寻常百姓倒酒端菜,让后者在啜酒小食的时候,暂时忘却浮生烦忧,享受人生简单的乐趣。这会儿,弄不清楚是第几代传人的掌柜,则以威尼斯人特有的一种有礼而疏淡的世故态度,款待着像我这样的外地游客,令我在满足了口腹之欲的同时,以为自己已捕捉到了历史。 我的隔邻站着位戴着呢帽的阿伯,想是常客,因他老人家一进门,啥也没说,只和掌柜的点个头,打声招呼,后者就倒了一杯红酒,送到阿伯面前。阿伯兴许察觉到好奇打量的眼光,侧身瞧了瞧只要喝上两杯酒就满面通红的我,并不以为忤,微笑着向我举杯示意,嘴里还说了什么,像是祝我健康。我自觉失礼,赶紧也举杯,回声 salute,祝您老身体安康。 醺醺然步出酒馆,醉眼模糊中,威尼斯的阳光似乎更加灿烂,水波也更加潋滟。我搭着丈夫的臂膀,眯着眼望着那青天下施施然而行的游人、运河上悠悠划过的贡多拉,还有河畔那一幢幢古旧却仍雍容华贵的老屋。起码在那一刻,我觉得这世界何其美好,因为威尼斯属于我,或者应该说,我属于威尼斯。 值得一再报到的小酒馆 威尼斯 osterie多不胜数,我当然无法一一造访,不过算一算,我在多次的威尼斯之旅中,起码光顾过一二十家跑不掉。下面介绍的,是经汰选以后,我和约柏比较喜欢的几家,我们每回到水都,一定会去报到。请注意,大部分小酒馆都是早上即开门,营业到晚间八九点就打烊。 osteria da lele是一家超迷你也超平民化的小酒馆,很有街坊小店的味道。整个店面大概两坪不到,小小的柜台前永远挤满了人,午餐时分人潮还会溢到门外的广场上。我们当初就是被这股盛况所吸引,而加入等候的顾客群中,当场就爱上这家连招牌都没有的不起眼小店。 两趟居游期间,我们不知去了多少回,有时只是各吃一份小点心,喝一小杯酒,有时则打包一牛皮纸袋的 panini,到公园野餐。年轻的老板到后来已认得我们,一看到这一对馋嘴夫妻就笑盈盈地打招呼。 da lele不但店面小,店里供应的 panini个头也比一般小,店家干脆称之为 mini,一个索价仅仅九毛钱,食量小的人吃两个大概六七分饱。 迷你 panini分量虽不大,质量却一点折扣也不打,面包绝对新鲜,而且外脆里软、很有嚼劲,里面夹的火腿、腊肠和烤猪肉,也美味异常,听说是年轻的店主亲自到乡下进货,精挑细选过的。 服膺“迷你”原则,这儿的酒一律用小小的 ombra杯装,选择并不多,红白酒各五六种,也是店主自个儿去产地向酒农采购而来,免除中间剥削,价钱因而也迷你,一杯才六七毛欧元,最贵不过九毛钱,比一般咖啡馆站着喝的 espresso还便宜。 店面袖珍,当然没有座位,大伙都是点了酒,买了食物,就端着木盘到门外,在广场上或河岸享用。只要没下雨,倒也别有乐趣。 由于所处位置并非观光客必经要道,这里的顾客除了零星的游客(好比我和约柏)以外,其他多半是老主顾。很多人一进门就直呼店主之名,大声问好,观其模样和打扮,应该是在附近打工的劳工阶级,另外还有不少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我后来才发觉,著名的威尼斯建筑学院原来就在小店所在广场的另一侧。 威尼斯住宅区的街坊小吃店,有的并不见得欢迎观光客光临,而偏好做熟客生意。但是 da lele亲切的店主并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就连店里的劳工和学生顾客也对我这个挤在他们当中等着买酒的游客,露出一副嘉许的神情,仿佛在说:“好样的,竟找得到这里呀。 ” osteria da lele 地址:santa croce 183, campo dei tolentini 水上巴士站:piazzale roma 周日公休 al marca也是家店面极小的小酒馆,但风格和 da lele大异其趣, da lele蓝领而粗犷,al marca则白领而都会,大理石面的木头柜台,正式的酒杯,咖啡豆选的也是较昂贵的 illy豆,整体上带着些许的雅痞气味。 al marca就在里亚托蔬果市场的一侧,附近还有法院和市府公务单位,人群川流不息,算得上位于黄金地段,再加上这儿的酒和 panini质量都还不错,价位亦适中,因此生意很好。上午时分,可以看到挽着菜篮或拉着菜篮车的老人和主妇,来这里小啜一杯;中午和近傍晚时,则换作上班族来吃午餐或喝杯饭前酒。此外,由于坐落的地点醒目,除了本地客外,爱到这儿来小喝一杯的过路游客似乎特别多。 这里咖啡也不错,我到里亚托市场买菜时,常会过来喝杯 espresso,吃块点心。他家自制一种很像法式 quiche(酥壳饼)的咸派,都蛮可口,菠菜奶酪口味的特别合我的胃口。 al marca 地址:san polo 213, erberia rialto 水上巴士站:rialto 周日公休 osteria al ponte这家小酒馆和 campo ss giovanni e paolo只隔了一座小桥,因此就取名为“桥头小酒馆”(ponte意即为桥),店门漆成鲜红色,很好找。这里的酒种类不算很多,但基本款都有,我在这儿喝过的几种红、白酒,品质都不错。木框玻璃柜里摆的小菜和 panini,样数也不很多,但亦精美可口,我尤其喜欢西红柿肉丸和夹了风干牛肉的三明治。小店设有木桌木椅,不喜欢立食的,可以舒舒服服坐下来,享用酒肴,不加收台布费。 我头一回光临桥头小酒馆,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当时它还名不见经传,上门光顾的多半是本地客人,因为店面不算大,就靠店主一个人也忙得过来。当时和我一起去的里欧,是个很爱哈拉的家伙,结账时他开玩笑地建议店主最好去学中文,以后也许会有更多台湾人跑到他店里来,因为这位小姐(这家伙说着便指指我),是个写食物的台湾记者,“老板你搞不好会上报哦”。 记得店主当时只是微微笑着,道了声谢,说不定他对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赞美早已习以为常,也说不定就只是个性内敛而已。 这么舒服、价钱也公道的小酒馆,我才不要大肆报道呢,只想悄悄和朋友分享,把它当成大伙来水都吃喝玩乐的一个小小据点。 然而,不需要我的宣传,好店不会被埋没,小酒馆如今已获包括《孤星》在内的数本旅游指南推荐,生意可比十年前好多了,本地熟客照来,游客也开始上门。眼下店里平日由两个年轻伙计负责打点,我们两次居游期间都没碰到店主,后来才知道,他只有周末才会来店里照顾生意。 不同于一般小酒馆,这里下午四点左右到六点多不营业,晚上则供应pasta之类的热食晚餐,打烊时间也比一般小酒馆晚很多,不过我们并未在这儿吃过晚饭,不清楚水平如何。 osteria al ponte 地址:cannaregio 6378, calle larga giacinto gullina 水上巴士站:ospedale 周日公休,午餐与晚餐时段之间休息 bancogiro是一家少数在周日营业的小酒馆,小菜样数少但精美,我们曾在那儿吃到极嫩极香的溏心蛋,到现在都想不透,不过就是白水煮鸡蛋淋点橄榄油、撒点盐和胡椒嘛,怎么 bancogio竟能这么好吃? 这里酒的选择很多,质量也上乘,我们在这里喝到非常好的意大利霞多丽白酒,一杯就要四欧元,以小酒馆来说,并不算便宜,但物有所值。店家也备有多款不到两欧元的平价酒,亦不错,大体上是家令人放心的酒馆。 这家酒馆有厨房,供正餐。夹层二楼设有桌椅,为用餐区。天气温暖时,店后紧靠着大运河的空地亦摆设餐桌椅,可以让人一边吃饭,一边欣赏河上风光,气氛绝佳,因此夏日的夜晚,这儿总是座无虚席。 bancogiro 地址:san polo 122, campo san giacometto 水上巴士站:rialto 周一公休 cantina do mori这家创业于一四六二年的小酒馆,很为它悠久的历史自豪。店内灯光晕黄,装潢古色古香,天花板上悬挂着各式各样古旧的铜锅,总之就是想方设法要营造一股古老的气氛。 我和约柏都认为,这家的小菜是我们试过的各家酒馆之冠,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同样的菜色,他家烹调出来的滋味就是比别家细腻,或许是善于选料之故吧。 我每回到这里,都免不得要小小苦恼一下,因为每一样看来都很好吃,真不知该选什么,所以每次都超出原本的计划,多点两样解馋。 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超群的水平是要付出代价的, do mori的价位硬是各家酒馆之首,别家一份一块多欧元的小菜,这里大概要两欧元。可是顾客只要来过,应该都不会介意多付点钱吃好东西,连时常埋怨观光客害得本地物价高昂的本地人,不时也会来这儿喝上一杯。我每回到 do mori,它的生意都一样兴隆,游客和本地客在狭小的店内摩肩接踵,大伙儿乐陶陶地大啖美食佳酿。 do mori的酒价位有高有低,平价的例牌酒并不贵,单杯不到两欧元,质量不错, fragolino甜酒亦好喝。惟一美中不足的是, prosecco用浅香槟杯装,而非细长的 flute,因此较易走汽。 do mori除了靠墙边勉强摆了几把高脚凳外,别无其他座位。 cantina do mori san polo 429, sotoportego dei do mori 水上巴士站:rialto 周日公休 cantine del vino gia schiavi这家酒馆位于贡多拉船坞的斜对岸,供应多种好吃的 panini,bacalà mantecado(咸鳕鱼酱)抹面包非常美味,例牌 prosecco蛮好喝。 店里小菜有名,酒更出名,既是酒馆,也是葡萄酒专卖店,有很多本地人来这儿买整瓶的酒外带。这店里收藏了不知多少种酒,有贵有贱,满足不同的需要。店面里头摆的多半是中等价位的酒,以意大利各产区的葡萄酒居多(当然),店后则有个收藏较高价佳酿的酒窖。 这家酒馆夹在两个水上巴士站之间,邻近还有威尼斯大学的讲堂,地点便利,生意非常好,有不少过路客,也有大学来的常客。店家未设座位,在柜台点好你要的酒和小菜后,或就站在柜台前或墙边的长条架旁享用,天气好的时候,则索性端着酒菜到门外,把河岸的矮墙当桌子,边晒太阳边就着佳酿美点,谈天说地。 cantine del vino gia schiavi 地址:dorsodoro 992, fondamenta maravegie 水上巴士站:zattere或 accademia 周日公休 喝葡萄酒就是要这么率性 意大利人喝酒,通常比较不拘小节,也不像法国人那么讲究“品酒”。对许多意大利人而言,酒和食物是分不开的,吃饭时少不了酒,喝酒时也必得配两样小菜点心才像话。 还有人甚至不理会红肉配红酒,白肉和海鲜佐白酒的这一套所谓通则,吃猪肉、小牛肝配白酒,食鲔鱼、鲑鱼佐红酒,都是常见的配法。夏季天气炎热,意大利人甚且会把红酒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喝,法国人和葡萄酒“达人 ”看在眼里,恐怕会不以为然。可意大利人喝酒就是这么率性! 威尼斯人也不例外,而且威尼斯人似乎特别爱小酌两杯,从城里遍布着小酒馆便可看出这一点。你很少会看到威尼斯人喝酒而不吃东西,因此在威尼斯的小酒馆,酒和小菜地位同等重要,再不怎么注重菜色的酒馆,起码也会备上精选的火腿腊肠和奶酪,还有小酒馆最基本的菜色──水煮蛋淋橄榄油,供客人下酒。 威尼斯人虽好饮好食,但陆地狭小的威尼斯其实并不产酒,不过所在的威尼托地区,却是意大利的重要葡萄酒产区,白酒产量尤其多,其中又以 prosecco汽泡酒最被称道,为威尼托的代表酒。这一点和威尼斯紧傍潟湖,威尼托人嗜食海鲜,或许不无关联。 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公认威尼托最优质的酒,并不是较适合佐鱼和海鲜的白酒,而是近年来售价之高不亚于法国波尔多的红酒 amarone(阿玛罗尼),根据葡萄酒专家推荐,顶尖的酒庄包括 allegrini、serègo alighieri、brunelli、dal forno、masi、speri和 tedeschi等。 葡萄酒铺沽酒乐 居游水都有个怡人乐趣,就是到葡萄酒铺沽酒去。 这些卖酒的小店有的叫 cantina xx,有的叫 vinaria yy,译成中文就是某某葡萄酒铺,有些则连店招、店名也没有。 这类葡萄酒铺除了销售一般常见的瓶装葡萄酒外,最特别的是也卖散装葡萄酒,但不供应可在店里饮用的单杯酒。有些位于住宅区的酒铺,为了方便邻居,也顺便卖矿泉水、面条、西红柿酱汁之类的日常基本杂货,货色不多就是了,毕竟正业还是卖酒。 酒铺里头必然安放着一樽樽细颈大肚的深色玻璃坛,里头装的都是平价葡萄酒,有红酒也有白酒,当然也少不了威尼斯人热爱的普罗塞克汽泡酒,这些统统可以零买。 买散装酒最好自备容器,塑料瓶、空酒瓶都可以,你拿着瓶子到店里去,选好你要的酒,店家就会拾起酒坛上附着的一条像水管一样的管子,替你把容器装满,不管红酒白酒,一律照容量计价。假如你没有容器,店家也可提供,多半是装矿泉水的塑料瓶。拿不定主意要买哪种酒时,也可请教店家,只要说明自己打算用来搭配什么菜,对方就会给你建议。 散装酒一般售价为一公升两欧元上下,当然不大可能是优质佳酿,尚可入口而已,对付着日常佐餐用,勉强过得去。 不过,在我看来,酒的质量其实并不很重要,因为买散装酒的主要乐趣并不在于酒,而在于买酒这件事本身,更精确一点说,是那份古风。我每回拎着洗干净、晾干的酒瓶,到葡萄酒铺去沽酒,都觉得好像回到了古代的苏州或是扬州,真想学武侠片里的女侠,把酒瓶往酒肆的柜台一放,跟卖酒的说:“掌柜的,来一斤黄酒。 ” 威尼斯仍有为数不少的散装酒铺,有个体经营的小铺子,也有连锁加盟店,名为 nave de oro。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迎面走来的行人,手里握着装了葡萄酒的塑料瓶,或附近有人拎着空空的塑料瓶,往某个方向走,这时不妨多留心一下两旁的店面,说不定就会看到一间古意盎然、没有招牌的小店,里面摆着一樽樽的大酒坛,记住它的位置,下回也自备空瓶来沽酒。 威尼斯葡萄酒推荐一下 在威尼斯,你常会看到、喝到的葡萄酒,有下列几种: 红酒 (vino rosso) *amarone 产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verona)一带,是种不甜且强劲厚实却不失圆润的红酒,后味略苦,适合搭红肉与野味。 *bardolino 产于维罗纳西侧嘉达湖(largo de garda)周边地区,是种清淡的红酒,配红肉和禽肉皆可。 *valpolicella 亦为清淡的红酒,公认产自瓦尔波利塞拉(valpolicella classico)地区的较好,适合配火腿腊肠、牛肝菇(funghi porcini)或西红柿酱汁。 ◎白酒(vino bianco) *bianco de custoza 产于嘉达湖地区,是柔和、芳香且不甜的白酒,配上海鲜一级棒。 *prosecco 威尼托的代表性白酒,产于威尼斯北边特雷维索(treviso)一带,是富含果香的清淡汽泡酒,区分为不甜(secco)、微甜(amabile)和甜(dolce)三种。管他红肉、白肉或海鲜,威尼斯人吃什么都可以配prosecco。 *soave 产于维罗纳以东地区,是种不甜的白酒,因产量大,是最普及的威尼托白酒,优质佳酿风味优雅,可惜有很多滋味平庸。soave适合当开胃酒,亦可搭配蔬菜、海鲜和清淡的面食。 另外,维琴察(vicenza)以北breganze产区的红白葡萄酒,在威尼斯也是到处可见,有不少餐厅采用的例牌酒,就来自这一带。 白酒包括有以tacai葡萄酿制的breganze bianco、pinot bianco和pinot grigio等三款果香浓的白酒和较清冽的vespaiolo,这几款酒都适合配开胃菜或海鲜和鱼肉。 在红酒方面,breganze rosso和cabernet适合搭配红肉或味道较浓的酱汁。pinot nero较清淡且有果香,可以拿来佐鸭肉和雉鸡等禽肉。 …… 韩良忆 作家,生活美食家。定居荷兰,云游四海。 喜欢简单的生活,认为生活中只要有好吃的食物、好听的音乐、好看的书和电影,平日能在家附近散散步,一年至少去旅行一次,就很好了。 著有《在欧洲,逛市集》《我在法国西南,有间小屋》《我的托斯卡纳度假屋》《在郁金香之国小住》《吃东西》《韩良忆的音乐厨房》等作品。
作者: (法)马赛尔·海德里希(Marcel Haedrich)著;治棋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9
简介: 本书作者马赛尔·海德里希收集了服装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的诸多 回忆与秘密。而香奈儿小姐更是史无前例地向他尽诉衷肠。 她的极富传奇色彩的坦率、她的幽默、她的童年隐私、她的青春时代 ,她独步天下的创作方式,以及她的爱情,无不令这部远非普通传记可比 的经典之作释放出铿锵的律动,律动出香奈儿浪漫的一生。 更何况,无论是银幕上还是荧屏中,多少位名动天下的表演艺术家早 已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她的人格,是的,香奈儿是不朽的。
作者: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著,周克希(译)
简介: 本雅明曾说,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特例,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在这些特例中,属于最深不可测的。这部七卷本的巨著被誉为“最美的文字,最难读完的小说”,是法国文学的象征,它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把神秘主义者的凝聚力、散文大师的技巧、讽刺家的锋芒、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并且写得令人兴味盎然。仿佛从未有一部作品,具有如此丰繁的复杂美,却同时又如此地明晰而优雅。为了尽可能地让读者领略到普鲁斯特独特文体的魅力,《〈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是著名法语翻译家周克希先生在保留情节主干的原则上选译七卷本而成,采用“大跨度”的节选方式,即先在整部小说的每一卷中,分别选取特别精彩的大段,每个大段的文字一字不易,完全保留原书中的面貌,然后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连缀这些段落,并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从而使读者能够领略原汁原味。 同时还附赠一份全彩别册《普鲁斯特纸上展览》,由普鲁斯特研究专家涂卫群老师撰文,以普鲁斯特一生居住、生活的地点为纲要,勾连当时的时代风貌、艺术文化风情,力求完整而全面地展示普氏以及其著作的时代意义。
作者: (法)马赛尔·马尔丹(Marcel Martin)著;何振淦译
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简介:作者从电影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为论述起点,讨论了电影语言作为叙述故事和传达思想的手段,它一方面极其丰富多彩,同时也很复杂,它能够灵活而准确地重现事件、重现感情和思想。对电影语言的不同运用,体现了导演的风格。全书十三章,作者引用上百部电影为例,生动地阐述他的论点,使本书内容充实,可读性强,是学习电影艺术、研究电影理论的学生和专业人士的必备书籍。
追忆似水年华 Swann’s Way Rememberance Of Things Past 马歇尔·普鲁斯特著 最经典英语文库
作者: 马歇尔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年01月
简介:
马歇尔?普鲁斯特 (1871-1922)原名叫Valentin Louis Georges Eugène Marcel Proust,汉译大概为“瓦伦廷?路易斯?乔治?尤金?马歇尔?普鲁斯特”,不过,人们一般都只称他为马歇尔?普鲁斯特。他是法国人,因为写出了这本《追忆似水年华》而一跃成为法国*有名的小说家。同时,他也是文学评论家、散文作家。《追忆似水年华》以七大部分,于1913年到1927年陆续出版。现在马歇尔?普鲁斯特被公认为20世纪*伟大的作家之一。
法文共同题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作者: (法)M.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著;徐和瑾,周国强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2
简介:本书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文学创作上的新观念和新技巧。小说以追忆的手段,借助超越时空概念的潜在意识,不时交叉地重现已逝去的岁月,从中抒发对故人、往事的无限怀念和难以排遣的惆怅。
Basic principles of membrane technology
作者: (荷)[M.米尔德]Marcel Mulder著;李琳译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简介: 内容简介 膜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中的分离、纯化和浓缩过程。本书是有关膜技术的综合性教科书。 全书包括8章:绪论、材料及材料性质、合成膜的制备、膜的表征、膜传递过程、膜过程、极化现象和 膜污染、膜器和过程设计。 作者是荷兰Twente大学膜科学和技术中心的专家。他在阐述膜技术原理的同时引用了大量的实 例,每章末附有丰富的习题并有解答。 读者对象:大专学生、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简介:本书是由莫斯有关技术和技艺方面的论述所构成的一本真正的全集,是一项深入、全面且相当具有开创性的成就。 本书内容几乎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中有关技术的所有重要问题,从旧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与交换、殖民地田野点的调查,到物质文化(莫斯和他的同事都没有使用过“物质文化”一词)的社会和象征意义;小到吃饭、走路、坐姿,甚至是睡觉,都不能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些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文明中,成为他们相互区分的标识。
作者: (法)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著;佘碧平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简介:马塞尔·毛斯(1872.5-1950.2)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交换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曾作出高度创造性的比较研究,他的有关人种学理论和方法的观点也对许多社会学家产生影响。毛斯是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外甥,曾协助舅父编写过许多著作。本论文集编入了他的第一流的内容最丰富的社会学专题论文。他的“论礼物”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着重论述了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北美洲西北部等地土著民族的交换和契约形式,并对赠与、接受及偿报等行为的宗教、法律、经济、神话和其他方面予以探讨。该论文集的出版为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学习、查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a plant location and site selection guide
作者: (比)马塞尔·德·迈尔利尔(Marcel De Meirleir)著;赵巍,王冬梅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简介:商业选址泰斗50年经验 作者 —— 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 与多国政要直接交流选址经验 通过选址,协助比利时梅赫伦市将失业率从18.4%降到4% 成功实施伦敦著名市集移址项目 帮助通用电气等著名跨国公司多次成功选址 成功实施全球范围内1 500多个选址案例 选址决策知识的获得,只能来源于如下三个渠道:经验,经验,还是经验! 对管理层而言,选址决策的难度最大,影响却很深远。选址决策的方式往往事关企业的成败。 在所指导的1 500多个案例中,我们至今仍未尝败绩。因此,我们确信我们的建议是不无道理的。
作者: (法)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著;汲喆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本书作者马塞尔·莫斯是法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礼物》一书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莫斯对“礼物”的分析中,其根本问题是要探究人是如何与物以及通过物而与他人彼此互相关联的。通过对丰富的民族志资料的旁征博引,莫斯提出了以“整体性呈赠”为特征的“礼物经济”的概念,并与现代的、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换体系相比较,提出了一个三阶段式的演进图式,并进而探讨了物权与契约等经济概念的源起及本质。本书列入世纪人文系列之“袖珍经典”。
Spacecraft dynamics and control
作者: (英)西迪(Marcel J. Sidi)著;杨保华译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2011
简介: 《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译自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和特拉维夫大学的marcel j.sidi博士《spacecraft dynamics and control:apractical engineering approach》一书,主要介绍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卫星实践,重点分析和解决现实的工程问题。内容涵盖轨道动力学、姿态动力学、重力梯度稳定、单自旋和双自旋稳定、姿态机动、姿态稳定、结构动力学和液体晃动等。 《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不仅可用于航天领域工程设计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航天专业学生的教材。
简介: Music and art have gone together at least as long as there's been singing in church, but Sound & Vision opens in 1967, when the covers of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Peter Blake) and 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 (Andy Warhol) announced that musical collaboration with Pop artists was here to stay. It moves on to the artist-muse relationship, with attention to Robert Mapplethorpe and Patti Smith, who lead to Punk, New Wave and the artists of the East Village. In the 1980s, art-school musicians like the Talking Heads and Sonic Youth fused the primitive energies of rock with the intellectual refinements of art school, emerging with a unified aesthetic just as videos were rai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visual. Today, videos and art of all kinds continue to create and influence the market for music, and collaborations are thriving, from schoolmates Damien Hirst and Blur to partners Bjork and Matthew Barney and ur-hipsters Beck and Marcel Dzama. Sound & Vision observes the fertile mixing of photography, painting, music and video, a nod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nections that has slowly become a major influenc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oth pop music and visual arts. Includes works from Keith Haring, Julian Schnabel, Raymond Pettibon, Damien Hirst, Mike Kelley and Matthew Barney, among 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