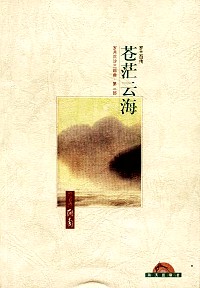共找到 3 项 “米高” 相关结果
作者: 蔡天新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7
简介: 新世纪之初,《南方的博尔赫斯》作者以数学教授的身份赴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最高学府访问。这座拥有300万人日的南美名城位于海拔1500米高的安第斯山上,有着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果实,迷人的光,艳丽的女子和花都、春城的美誉,并以醇香的咖啡闻名于世。作为”死亡之谷”的同义语,麦德林又是世界的毒品中心和大毒枭埃斯科瓦尔的老巢,装备精良的游击队时常出没在郊外的丛林中。同时,一年一度的麦培林国际诗歌节也在此举行,规模和听众人数堪称世界之最,作者作为推一的中国诗人应邀出席。 《南方的博尔赫斯》的前两章讲述了作者在麦德林九个月的亲身经历,中间三章则是有关作者在巴西、巴拿马、古巴、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的游历,最后两章谈到两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20世纪的文学巨人,其处女诗集被作者完整地从西班牙语译成了汉语;皮扎尼克是西班牙语世界顶尖的女诗人,有着与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一样传奇的经历,却在我国鲜为人知。 作者用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分析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作品风格,还介绍了第一个为拉丁洲赢得国际声誉的古巴画家拉姆,他的父系来自中国,以及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阿根廷革命家格瓦拉与哈瓦那的情缘。 作者以清雅、隽永的笔墨,从政治、经济、人文、地理诸方面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这个载歌载舞、遥远神秘的大陆。
作者: 丘彦明著
简介:彦明是老友了。1976年底,我自欧洲回台,当时在《雄狮美术》任职,不多久就认识了彦明。她学编采,毕业后进报社,成了副刊的重要帮手。不多久,《联合文学》成立,彦明担任编辑,是这本文学杂志草创时期重要的策划者与执行者。 彦明个子小小的,体弱多病,总见她不停咳嗽,一脸倦容。但她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毅力惊人。跟她熟悉起来之后,常常半夜三更接到她电话,人还在报社,还在为某一篇稿子做编排,或策划一个新主题。工作执著认真至此,令人叹为观止。大概有一段时间我遇到彦明,惟一的叮嘱就是:“休息了。”或者凌晨一两点打到她办公室试探,如果果然是她接的(其他人都下班了),我二话不说,即刻下令道:“回家睡觉了。” 工作繁重,有做不完的事,但或许是彦明天性中一份“痴著”,使她种种事皆放不下。有朋友敬重疼惜,当然也有不了解的人引以为是非罢。在彦明一次大病住院时,她刚动完手术,心力交瘁,我有不忍,便极力劝她辞职出国,能够真正静修一段时间。1988年,到布鲁塞尔看她,彦明已笃定自信,又学画又学音乐,如神仙般快乐,恰好又遇到她们家旧交的子侄辈唐效自荷兰来看彦明,三人同游数日。告别时我便私下和彦明开玩笑说:“这个人,你若是不嫁,这辈子就不要结婚了。”不多久,他们成婚,是我心中最快慰的事之一。 彦明厚道,所以屡经波折,毕竟也遇到珍惜她“痴著”的人。别人说彦明命好,我只回道:“彦明厚道。” 婚后家居荷兰,我到欧洲,绕去他们住的小城,盘恒数日,大家话都不多,但他们的生活,宁谧安静,平淡而知足,是在台湾时的彦明难以想像的罢。在考克小城,白日唐效上班,我和彦明到森林闲逛,采些野菇,彦明租了农地,兴冲冲带我去摘各类菜蔬香料,一方面问:“晚上做什么菜?”一方面喜孜孜东张西望。我知道这片土地上一根葱、一把芫荽都是她另一种“痴著”,心里想:这样疼惜菜,菜是做不好的。果然,回到家,她就把一把细嫩的青葱像洗女王的头发一样洗啊洗的,又欢喜赞叹地摆在木砧板上,拿了一把小刀,比做雕刻的人还要钻研地切成细细葱花。我开玩笑说:“你种的不是菜,是文学。” 她果然拿出笔记本,里面用彦明才有的蚂蚁般细密的字体,工工整整记录着整个农地上的作物。还有素描的图绘配合,我知道,这一份与土地自然的“痴著”将是彦明这些年值得与大众分享的幸福罢。 第二天,经过一个陌生的园子,大蒜长得有一米高,粗壮肥大,咄咄逼人,而且抽长擀面棍粗的蒜苔,我大叫:“蒜苔!”主人闻声出巡,我们告知他这是好吃的东西,可以炒腌肉,主人似乎不信,但随手抓起,连根带土抛给我们,回家终于吃了一顿大快朵颐的晚餐。 想起这些事,又是许多年过去,彦明的“文学”终于要结集出书了。刚过二千年,她与唐效回台湾,交给我稿子,嘱我为序,我想,彦明此时锄田掘土,一定也有豁豁的风度了罢。相信彦明这本书将带给朋友健康愉快的生活经验。
作者: 罗兰著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8
简介:“聚泰号”。 “聚泰号”是高祖父时代所开的粮店。 传说,高祖父兄弟二人随祖上从浙江绍兴移居北方。赤 手空拳,来到芦台谋生。先是在亲戚的住家门外屋檐下摆个 小摊卖粮食,所赚的钱虽然很少,但兄弟二人人缘极好,做 生意诚实不欺,空闲时就念念书,很得主顾的信任。二高祖 父特别喜欢文墨,练就一手好书法,常给乡人写写对联,渐 渐有了名气,结识了地方上的仕绅,经人推荐,进了县府做 师爷,撰写公文,得到县府的重用。大高祖父坚守本行,积 存了一些本钱,开了正式的粮店,就是“聚泰号”。 “聚泰号”给这两兄弟带来财富,以后又继续经营了其 他生意,开了木厂、首饰楼、药铺、还有一家黄酒厂,都以 “聚”字排名。他们也置了许多产业,包括十几所瓦房,本 县和外县的庄园土地,芦苇地等等,逐渐成为当地首富。家 中所住的这栋大宅,位于北街,后临蓟运河。中间四层大四 合院,两旁是东西两个跨院。第五层是横跨三个院落的大花 园。 祖父那一代,是最承续祖上余荫的一代。那大约是清末 同治年间到光绪年间,外侮不断,鸦片烟久已荼毒全国。民 间不但无法抗拒烟害,反而形成一种风尚,许多有钱人领先 追赶这时尚,祖父一代也有几位染上烟瘾,视为富贵的象 征。加速了家道的衰败。到了父亲这一代,不但“聚泰号” 已不存在,只剩下字号名称;所经营的其他生意也都已经倒 闭或出让。田地庄园大部分典当质押,房产也只剩下了蓟运 河畔,我们所住的这所大宅。所幸到了我父亲、伯、叔这 代,不约而同地奋起经营,不再挥霍,拒绝不良嗜好,各安 本分。能出外求学的出外求学,学成之后,有人出外做事, 有人自愿守住家园,拯救家业,放弃向外发展的机会,在家 照顾所剩无几的田庄。对内节衣缩食,对外却尽量维持“聚 泰号”的声势,绝不在乡里间露出败相。一切婚丧大典,绝 不马虎吝啬,竭尽所能,照以往的排场办事,而且绝不举 债。 多年来,家中的伙食,用我们自己的话来形容,是“咸 菜拌豆腐,豆腐拌咸菜”。天天小米高粱,对外却一丝不苟 地撑住了场面,连祖上对清寒亲戚的接济,也丝毫不减,年 年照以前的规矩办理。居然熬过了各种战乱,而且逐渐赎回 了典当质押的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家中几乎 可以说是恢复了元气。逐步走向振兴的途中。 这“靳向善堂”第四代的力图振作所显示的意义,与其 说是为了恢复当年的荣华,不如说是基于一份根深抵固的中 国伦理。做为后代子孙,先天有责任振兴家业与保护家声。 否则便是“不孝”。伯、叔与父亲这一代,正是这样令人起 敬的一代。 我是这家中第五代的第一个小孩。 出生在家道衰微与力图振作的交替时代,懵懵懂懂,成 了这所大宅中的一员。都市里,正在风起云涌,受到“五 四”新潮的强烈冲激。父亲和三叔、四叔都在天津就读新式 的学校。而芦台镇上,这保守的大家庭里,却还维持着从里 到外的平静如恒。我的母亲也仍然是和家中其他的妯娌们一 样,在这严守旧礼的大家庭做媳妇,既没时间也没心情来照 掉头不顾而去,我的感觉是:“既然无能为力,不如离开这 拷问吧!” 我一口气放弃学业,辞掉工作,离开家庭。特别是那学 业。期待了八年的重叩大学之门的梦想,实现时却是那样的 残破不堪。也许,任何尘封太久的旧梦,都不应该希望去重 拾吧?既然如此,我不必再去注册了。那学业,就停留在 “音乐系,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因旷课太多而国文要重修, 体育要重修”的成绩单。对我这久已习惯了接受种种失望的 “大”学生来说,无足轻重。扔掉那成绩单,正如我扔掉二 十九年的岁月,好好坏坏,可以完全随它去了。 你不能不说,凡事皆有天定。 在我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觉得自己既然放弃了一 切,也只有远走台湾是较成熟而又浪漫的打算的时候,我一 点也不知道究竟要怎样,甚至什么时候才可以迈出这重要的 一步。 这天,时局混乱的北方,倒也依然是春风送暖,我坐火 车由塘沽到天津去,想试试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帮助我 下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你大概也经验过这种茫然的心情。当 自己并不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只能这么茫然地 暂时飘浮着。 塘沽是我的“第二家乡”,是我念小学的地方。天津是 我“第三家乡”,是我念师范学校,随家避日祸,以及在艰 苦中工作和经历人生风浪的地方。两处寄放着我不同的年龄 与不同的感情。而这次,我离开塘沽的家,到天津去,却是 我刚刚斩断了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全心空空如也的一个阶 段。 塘沽到天津,火车只需一小时。 北方春天的风沙,我是十分熟悉。敞开的车窗,照例吹 进满车厢的,属于北方的豪迈与迷茫。 斜对面,隔着走道,坐着一位乘客。他那温和自信的样 子,整洁不俗的衣着,立刻和我小时候的一个印象相重叠, 我几乎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位小学同 学,比我高两届。 我试着请对面的乘客替我问他贵姓,果然,他姓徐。于 是,我问他:“你是不是叫徐文朴?” 果然是他。 我们都很兴奋,不仅是因为在火车上巧遇,而且因为我 们已经从小孩子变成了三十岁左右的成年人,我却能立刻认 出了他,而且叫出了他的名字。 他并没有立刻想起我。女孩子变化大,而且我比他低 班,当年一定百分之百是个土土的小女孩。不会吸引他的注 意。而我告诉他,他现在和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完全没有 改变。他带着一分不可置信的神情,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 空位上,开始和我快乐地聊天。 二十年的岁月,当然说来话长。然后他问到我的近况, 我告诉他,我过得越来越黑暗,正把一切都放弃了,打算到 台湾去。 “你有没有买船票?”他问。 我连具体地该如何去台湾都还没有打算,又怎么会去买 船票?而且我根本也还不知道船票是该如何买法。它是和买 要求。 战乱与国仇,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离乡背井,不得不面对 投笔从戎。拜别爹娘的那一刻,他们的心情是慷慨赴义,而 不是儿女情长。他们的年龄在战火与离别中增长。他们的岁 月里,写满了抛弃与割舍。他们的日记里,写满了对自己的 鞭策: “你爱你的父母、兄弟妹妹,因而舍不得他们吗?不, 你要和他们分开!无论你是被迫或自愿。” “你爱你的爱情吗?不,你要和他分开,无论你是被迫 或自愿。” “你要婚姻吗?不,你爱的不一定能属于你;你拥有了 他,你不一定能给他幸福,无论你是被迫或自愿。你们的小 小炉灶没有安全与安定。也许在某一次流离中,你们永远不 再相见了;也许你到了天南,他到了地北,再相见时也不是 原来的你和他了。” “也许,你们的孩子在大家抢登某一班挤得不堪负荷的 列车时,被遗落在车站上了。也许,被遗落的是你的妻子或 丈夫。” “你已一脚踏入了那使你今后可以青云直上的校门了吗? 对不起,你要让一让。战争来了,学校在炮火下碎成齑粉, 你的学业前途之梦,也就碎成齑粉。你只能对自己说,梦碎 的代价是,你奔赴了一个令你觉得自己更崇高、更神圣的理 想。” “你的父母年迈体衰,他们曾经那么爱你、照顾你,对 你寄以厚望。你曾对自己发誓说:‘我一定要孝顺他们,奉 养他们。’你做到了吗?没有,没有。你为了奔赴一个更崇 高的理想,你要为国家献身,为民族效命。于是,那年迈父 母倚闾目送你远行的一个镜头,就永远在那里‘停格’。” “你曾想念过他们吗?在长长的岁月里,你曾为自己的 不孝而不安过吗?没有,好像没有,似乎没有,大概没有。 ……你不敢肯定,不敢深入反省。你假装什么也不曾发生, 你不想追问自己。也许,在梦中,你曾哭泣。但醒来之后, 你活在更清明的理智监督之下,你不去想自己究竟是在什么 样的感情之中。” “你努力让自己豁达,你看轻这一切人间世的苦乐。你 把一切个人的悲欢看作毫末,你承认人很渺小,于是,学 业、事业、爱情、婚姻、父母子女的亲情,当然都更微不足 道,更是沙尘。于是,你活得开朗而坚毅。” “你是这样的善于克制自己,你只要不让自己悲伤,就 可以不悲伤;你不让自己怀念,就可以不怀念;你不让自己 牵恋,就可以不牵恋。” …… 从民初到50年代的炮火,每次行动的纲领或许有所不 同,颠沛流离的滋味却是没有两样;渡海来台时的背景即使 每人不尽相同,一个海峡的彻底隔绝,却是没有两样。所隔 绝的,在一切现实的意义之外,对“人”来说,不是别的, 而是“感情”。 这一代人们,无论他是在海峡的哪一岸,在一生的岁月 里,所努力以赴的,是救国与建国;而在这慷慨悲歌的漫长 生途之中,他们所拼命围堵的,却是个人的感情。他们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