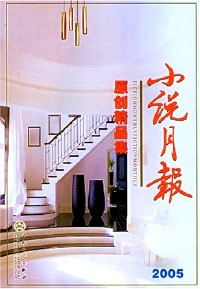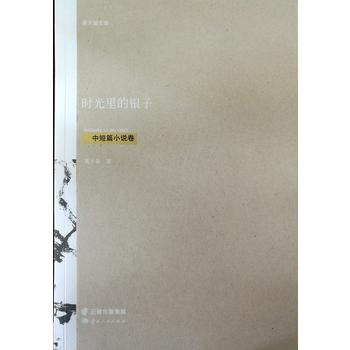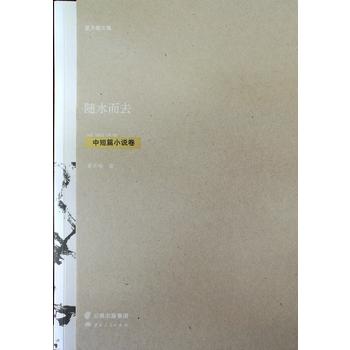共找到 30 项 “夏天敏”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简介:《小说月报·原创版》从2003年创刊至今已历时七年,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品牌,出版一套优秀作品丛书的时机已经很适当了。这套丛书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子,均是刊登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的小说精选而成。这些小说一经发表均在社会产生很大反响,或被多家刊物转载,或改编成影视剧,均为贴近现实,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小说作者阵容强大,作品质量上乘,加之《小说月报》的品牌效应,相信会有很好的市场。本书是《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之一,其中包括王祥夫《桥》、秦岭《皇粮》、夏天敏《拯救文化站》、陈应松《农夫·山泉·有点田》等,题材均是与农村农民和农业相关。全书约35万字。文字可读性强,雅俗共赏。
作者: 夏天敏著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
简介: 《接吻长安街》是夏天敏老师近年来的优秀短篇合集,收录了《月色晦明》《下山去充电》《漫过花园洋房里的浓烟》《拯救文化站》《接吻长安街》《冰冷的链条》《讨债》《在那无聊的日子里》等精彩短篇。
作者: 夏天敏著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一位生活在中国贫困山区的德山老汉,一辈子勤勤恳恳地种地,却从没有人拿他当回事。直到有一天,他意外获得了一对外国进口高级羊,才感觉自己受到了全村人的重视和瞩目。从此,德山老汉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但又催人泪下的故事…… 中篇小说集《好大一对羊》包括《好大一对羊》、《银簪花》、《土里的鱼》、《接吻长安街》、《猴结》、《在那无聊的日子里》、《北方心绪》、《拯救文化站》和《利民闸》等9部中篇。这些作品,是夏天敏近两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整体总结,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见作者创作的精神探索和心路历程,可以看见作者在坚持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弱势群体,关注 “三农”题材,以博大的胸怀和悲悯意识,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参与意识,继续书写着在社会变革时期,广大人民的悲喜忧愁,书写他们的精神风貌、内心的倾述和理想与生存状态的矛盾冲突。
作者: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 《小说月报》创刊于1980年。是我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最高月发行量曾达180万册,现仍居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首)、最为海内外各阶层读者喜爱的文学选刊。几乎所有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中青年作家的名篇佳作都是通过《小说月报》的及时选萃、推荐而走向全国,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的轰动效应。作为选刊,《小说月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即选得快、选得准、选得精和多样化。特别是注重选发贴近现实,紧扣时代脉搏,格调高昂,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作品,使刊物既厚重沉实又丰富多彩,既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欣赏需要又照顾到专家学者研究鉴赏之需。本书是《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的精品集,云集了十六位当代走红的作家的作品,约50万字,可读性强,雅俗共赏。 本书收集了2005年小说月报原创版的精华部分,收入有当今著名作家石钟山、、李铁、王祥夫、孙春平、李国彬、凡一平、衣向东、马步升、严歌苓、夏天敏、映川、阿宁、李锐、刘恪、聂鑫森、鬼子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并配有作者小传。
作者: 刘廉昌著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研究昭通作家群的创作思想的演变发展,是研究昭通文学现象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创作思想指导、规范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这不仅能够解释作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作家。 创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研究创作思想不仅有利于作家更好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创作历程,总结艺术经验,而且有利于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并把它植根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本书是第一本评介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的专著,该书作者二十年磨一剑,在对曾令云、夏天敏、蒋仲文等30多名昭通本土老中青作家作品研究和赏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昭通作家创作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创作风格的论述,对昭通文学创作进行了总体透视,是一本见证、解读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的文学评论专著。
作者: 夏天敏[等]著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简介: 要看中短篇小说,就不能漏过本书。本书收录了新世纪小说获奖作品 。主要包括《好大一对羊》、《我们卑微的灵魂》、《北京候鸟》、《淡 绿色的月亮》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已发表过不少作品,在国内文 学届也小有名气。值得广大小说爱好者阅读欣赏。
作者: 夏天敏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05月
简介:是个寻常的日子,玉婉推开厚厚的木板门,古镇上的青石板路上还泛着幽幽的青光,一层乳汁似的浓雾低垂在房屋的下面,使得古镇的房屋飘飘渺渺,虚虚幻幻,仿佛仙境似的,这景观也就是万壑丛山、绝壁之上的古镇才有的。玉婉起得早,宿在她店里的马帮和挑夫天不明就要上路,马锅头和挑夫已经在绿豆石凿成的盆里掬水洗脸了,关在客房后面的马厩里的马也被牵出来了,马们在清晨的冷冽的空气里打着响鼻,马锅头把抬出来的货物连同驮子抬上马背,玉婉抬出一簸箕桐叶猪耳粑,猪耳粑冒着热气,香甜的气味立即弥漫了院子。
作者: 夏天敏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04月
简介:
《时光里的银子》是夏天敏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在作品中,收录了作家精心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时光里的银子》《绿碑》《七夕》等中短篇小说9部。夏天敏善于编辑故事,提炼主题。基本上在每一篇小说当中,作家既有诗意的描写,又有泼辣的口语,形象与心灵、结构与节奏融合无间。夏天敏的叙述语言百转千回,生动多彩,富有弹性,在乡土小说创作中独领风骚。
作者: 夏天敏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2016年01月
简介:
选录作者中篇小说八部:《好大一对羊》、《徘徊望云湖》、《接吻长安街》、《好大一棵桂花树》、《飞来的村庄》、《北方、北方》、《冰冷的链条》和《土里的鱼》,其中《好大一对羊》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作品均以贫瘠的滇东北高原为背景,在描写那里农村艰苦、单调、落后的生活状况和农民愚昧、保守的思想的同时,表达了新一代农民思变的强烈愿望。作者文笔老道、深刻,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反映了存在于当今农村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比如,要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脱贫问题、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贫困人口与濒危动物共同生存问题等。
作者: 点评;中国小说学会编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实、柔顺……然而她的这种传统“乡下女人”的身份,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果然,“五号病”(口蹄疫)就来了,猪被烧光了,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进了城,于是,一个“乡下女人”与“城市”的对话和冲突,也正式地开始了。 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米秋水的死,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凶杀”,而是误杀。确切地说,是缘于另一“乡下男人”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而这一切,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 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摆脱了一般“底层叙事”的粗糙和雷同。 与葛水平的“平静”不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陈应松的叙述话语,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浑浊、浓稠、莽撞、肆意、喷薄……但却热力逼人。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但在初读他的《太平狗》、《火烧云》时,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烫”着了。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朴素,不加雕饰,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不要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不用头脑去同情,而要用心灵去同情——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上的云霭。 《太平狗》和《火烧云》,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就不多提了,好在《吼秋》是发表在2006年的。《吼秋》基本上还是《太平狗》和《火烧云》的继续,但没有像《太平狗》那样把“城”与“乡”写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祸”,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促织》的现代版。小说的主人公是先知兼蛐蛐大王毛十三,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而他捉蛐蛐的技艺却备受官员们的赏识……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 陈应松的小说,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也是不透明的。小说的故事推进,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如细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绝不流畅,绝不润滑,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而不得不跟着他转,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多是断断续续,疙疙瘩瘩,没头没脑的,很难抻成一条直线——那是种不以脑中的“逻各斯”为轨迹,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还是那句话,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而是写给心灵的。 如果说“底层叙事”是对于“底层”的发现,那么王松的《双驴记》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记忆与小说,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人在回忆其经历时,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当然,小说又不同于记忆,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录。小说是对记忆的发现和照临,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文本化”。用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飞起来”。 《双驴记》是王松继《红汞》、《红莓花儿开》和《红风筝》之后,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但复仇的“参动者”,却由人变成了驴——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的驴。王松笔下的复仇者,一般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边缘人,而其复仇的方式,则又常常是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其中充满着智慧。《双驴记》里的两头驴,不是边缘者,而是落难者。它们“祖上”原是地主家的坐骑,本有着高贵的出身与血统,但到了文革时,却由于“成分”不好,而被排在了“黑五类”之后,成为黑六和黑七。驴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故事也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双驴记》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在《双驴记》中,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会笑的驴眼,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这些充满了智慧与想象的细节,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 与《双驴记》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锈锄头》,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不同的是,王松本人就曾是知青,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而出生于70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青生活,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越来越多的“经传媒”性的知青记忆,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构成了对话和互动。 《锈锄头》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有着浓重的“经传媒”性身影:下乡-返城-奋斗-成功-怀旧-回乡凭吊……这已是从小说里,从电视剧里,从网络里,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从这个角度说,李忠民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那么“经传媒”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相关文本”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刷了漆的“锈锄头”。 好在乔叶的《锈锄头》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与当下乡村现实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像是“叶公好龙”故事的知青版。 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我在读这篇小说时,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生怕乔叶一时糊涂,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好在乔叶不负所望,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 乔叶在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打火机》,但《锈锄头》里的那一锄头,让我觉得它比《打火机》更具小说的“文本性”。另外,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也更发人深思。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生产和消费?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还有关于“富人”的想象,读起来很搞笑。叙述者一“秀”再“秀”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飘飘欲仙”的“玉仙牌”床垫,在睡“海丝腾”、“邓禄普”、“金可儿”的人们看来,岂不就是土炕?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见“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发现”与“遮蔽”往往是孪生的。 而叶舟的小说《目击》,其实正是篇很“解构”的小说。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他去年有个短篇叫《1974年的婚礼》给我的印象就很深。《目击》以李小果、李佛、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而王力可为了替亡夫查找肇事逃逸的凶手,竟不惜每夜长跪街头,苦苦守侯那个神秘的也是惟一的现场目击者。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读解为对爱情的坚贞,读解为现代恩爱夫妻的珍贵范本。李小果更是由此而反观自我,在陪跪的一个个寒夜里,洗心革面净化灵魂……然而,由她们以巨大痛苦最终催逼出来的“真相”,却没有到达她们那里,而是极其轻易地被凑巧拿起话筒的浪荡子李佛听了个正着——王力可的丈夫其实是死于偷情,他的情人就是那车祸现场的惟一目击者。一个有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神话,就这样地被颠覆了。建构着神话的人,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略显遗憾的是,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包袱”之间,似有头重脚轻之嫌,且有些简单和直白。如能在“真相”与二李的私情、王力可“钢筋”般的“硬”与肖依的“冷”之间,再做一番微妙功夫,在“修辞”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则会更加意味深长。 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小说最寂千人一面,当年“个人化”热时,全是卧室、浴缸加自恋,把“个人化”弄成了雷同化;现在的一些“底层叙事”,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说《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写家庭悲剧的,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从故事表层上看,这是一个重新找寻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又将主人公引上了“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自我发现之旅。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之旅。主人公要“回忆”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一个弑父者。 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可能是最有意趣的了。这样一来“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遗忘是内心潜抑的结果,早年弑父娶母(小说中的“母”被年长一些的女孩阿夕替代)的欲望,长大后当然要被遗忘。但遗忘并不等于消失,而只是躲藏到潜意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了。“那个面貌忧伤”的“就像是从天边而来”的邮差,在给主人公送来记录弑父案件的邮件时,显得极其神秘——他显然就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送来了早年的残破记忆和梦……整篇小说都有如一个半睡半醒的怪梦,故事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轻巧地剥离了出来,时间、年代只是某种符码化了的标识,其指涉性已被适度地削弱了……读者被带进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情境之中。 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解读出一个弗洛依德式的箴言——每个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女作家笔下的“俄狄浦斯”,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化了装”的“伊莱克特拉”? 作为昔日“先锋”,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格非的新作《不过是垃圾》也是篇“解构”性的小说,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死亡,就像个玩笑,更像是一种修辞,身患绝症的李家杰自知来日无多,生命、财富、公司等等都将不再归他所有,就连死亡本身作为一种修辞也失去了打动他人的效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可笑了。作为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大学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追到手的女同学苏眉。苏眉清高、倨傲,一尘不染,一直以来都是李家杰等一班“浊物”心中的痛。李家杰决定临死之前去看一看这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神,于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已经变换了的语境中又一次进行了“对话”,而“对话”的结果则是:苏眉被“做掉了”——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神,在300万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浊物”。而李家杰所得到的,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李家杰的感叹,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 罗伟章《奸细》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绕,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窝囊。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奸细”的,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相反地,他的做“奸细”倒真有几分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让他欲罢不能。做“奸细”不一定就是“坏”人,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好”人——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坏、忠/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当学校沦落成市侩出没的大集,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反智主义”时,一切的忠/奸/善/恶亦不再泾渭分明——中学已成为一个“洪桐县”。 教育的异化,是个一点都不亚于“底层问题”的问题。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教育”已与求知相悖,而几年过去之后,中学未见其好,反倒连大学也有些“中学化”了。小说《奸细》的文本,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有些“问题小说”的影子,但又超越了以往的“问题小说”。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问题小说”的种种“政治正确”的超越,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小说惟一的遗憾之处,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没能洞穿这一“反智主义”游戏的深层。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他以一种很“文本”的方式,向我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命案高悬》是一篇颠倒了的探案小说,一般探案小说的“叙事语法”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丝拨茧,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而《命案高悬》却把命案的真相“高悬”了起来,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复杂的倒是“体制”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正是本该作为“苦主”的死者的丈夫。小说中惟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既非公安也非侦探,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祸头”——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尹小梅却被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耐人寻味的是,吴响作为“体制”中的一名小卒时,尽可以去欺男霸女狐假虎威,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好事”时,不但被清除到了“体制”之外,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 致此,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高悬”。 《蚂蚁上树》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蚂蚁上树”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的“镜像”,是蚂蚁群、蚂蚁阵、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远看上去就有如“蚂蚁上树”一般渺小平凡。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黑压压一片”,而小说《蚂蚁上树》则“发现”并放大了这个“底层”群体,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 “底层叙事”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恰恰是因为以前“文学”对“底层”的漠视,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06年写“底层”的小说里,还有像曹征路的《霓虹》,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品。 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异,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不过,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05年末转载于06年初的《金陵十三钗》,也无法与之媲美。当然,有些东方“羊脂球”式的《金陵十三钗》也还是很不错的,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05年的12月份,就不便选进06年的小说中来了。还是那句话,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惟愿其长如源头活水,清且涟漪。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实、柔顺……然而她的这种传统“乡下女人”的身份,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果然,“五号病”(口蹄疫)就来了,猪被烧光了,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进了城,于是,一个“乡下女人”与“城市”的对话和冲突,也正式地开始了。 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米秋水的死,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凶杀”,而是误杀。确切地说,是缘于另一“乡下男人”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而这一切,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 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摆脱了一般“底层叙事”的粗糙和雷同。 与葛水平的“平静”不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陈应松的叙述话语,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浑浊、浓稠、莽撞、肆意、喷薄……但却热力逼人。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但在初读他的《太平狗》、《火烧云》时,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烫”着了。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朴素,不加雕饰,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不要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不用头脑去同情,而要用心灵去同情——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上的云霭。 《太平狗》和《火烧云》,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就不多提了,好在《吼秋》是发表在2006年的。《吼秋》基本上还是《太平狗》和《火烧云》的继续,但没有像《太平狗》那样把“城”与“乡”写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祸”,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促织》的现代版。小说的主人公是先知兼蛐蛐大王毛十三,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而他捉蛐蛐的技艺却备受官员们的赏识……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 陈应松的小说,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也是不透明的。小说的故事推进,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如细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绝不流畅,绝不润滑,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而不得不跟着他转,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多是断断续续,疙疙瘩瘩,没头没脑的,很难抻成一条直线——那是种不以脑中的“逻各斯”为轨迹,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还是那句话,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而是写给心灵的。 如果说“底层叙事”是对于“底层”的发现,那么王松的《双驴记》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记忆与小说,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人在回忆其经历时,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当然,小说又不同于记忆,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录。小说是对记忆的发现和照临,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文本化”。用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飞起来”。 《双驴记》是王松继《红汞》、《红莓花儿开》和《红风筝》之后,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但复仇的“参动者”,却由人变成了驴——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的驴。王松笔下的复仇者,一般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边缘人,而其复仇的方式,则又常常是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其中充满着智慧。《双驴记》里的两头驴,不是边缘者,而是落难者。它们“祖上”原是地主家的坐骑,本有着高贵的出身与血统,但到了文革时,却由于“成分”不好,而被排在了“黑五类”之后,成为黑六和黑七。驴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故事也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双驴记》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在《双驴记》中,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会笑的驴眼,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这些充满了智慧与想象的细节,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 与《双驴记》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锈锄头》,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不同的是,王松本人就曾是知青,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而出生于70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青生活,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越来越多的“经传媒”性的知青记忆,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构成了对话和互动。 《锈锄头》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有着浓重的“经传媒”性身影:下乡-返城-奋斗-成功-怀旧-回乡凭吊……这已是从小说里,从电视剧里,从网络里,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从这个角度说,李忠民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那么“经传媒”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相关文本”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刷了漆的“锈锄头”。 好在乔叶的《锈锄头》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与当下乡村现实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像是“叶公好龙”故事的知青版。 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我在读这篇小说时,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生怕乔叶一时糊涂,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好在乔叶不负所望,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 乔叶在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打火机》,但《锈锄头》里的那一锄头,让我觉得它比《打火机》更具小说的“文本性”。另外,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也更发人深思。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生产和消费?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还有关于“富人”的想象,读起来很搞笑。叙述者一“秀”再“秀”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飘飘欲仙”的“玉仙牌”床垫,在睡“海丝腾”、“邓禄普”、“金可儿”的人们看来,岂不就是土炕?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见“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发现”与“遮蔽”往往是孪生的。 而叶舟的小说《目击》,其实正是篇很“解构”的小说。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他去年有个短篇叫《1974年的婚礼》给我的印象就很深。《目击》以李小果、李佛、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而王力可为了替亡夫查找肇事逃逸的凶手,竟不惜每夜长跪街头,苦苦守侯那个神秘的也是惟一的现场目击者。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读解为对爱情的坚贞,读解为现代恩爱夫妻的珍贵范本。李小果更是由此而反观自我,在陪跪的一个个寒夜里,洗心革面净化灵魂……然而,由她们以巨大痛苦最终催逼出来的“真相”,却没有到达她们那里,而是极其轻易地被凑巧拿起话筒的浪荡子李佛听了个正着——王力可的丈夫其实是死于偷情,他的情人就是那车祸现场的惟一目击者。一个有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神话,就这样地被颠覆了。建构着神话的人,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略显遗憾的是,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包袱”之间,似有头重脚轻之嫌,且有些简单和直白。如能在“真相”与二李的私情、王力可“钢筋”般的“硬”与肖依的“冷”之间,再做一番微妙功夫,在“修辞”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则会更加意味深长。 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小说最寂千人一面,当年“个人化”热时,全是卧室、浴缸加自恋,把“个人化”弄成了雷同化;现在的一些“底层叙事”,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说《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写家庭悲剧的,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从故事表层上看,这是一个重新找寻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又将主人公引上了“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自我发现之旅。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之旅。主人公要“回忆”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一个弑父者。 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可能是最有意趣的了。这样一来“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遗忘是内心潜抑的结果,早年弑父娶母(小说中的“母”被年长一些的女孩阿夕替代)的欲望,长大后当然要被遗忘。但遗忘并不等于消失,而只是躲藏到潜意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了。“那个面貌忧伤”的“就像是从天边而来”的邮差,在给主人公送来记录弑父案件的邮件时,显得极其神秘——他显然就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送来了早年的残破记忆和梦……整篇小说都有如一个半睡半醒的怪梦,故事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轻巧地剥离了出来,时间、年代只是某种符码化了的标识,其指涉性已被适度地削弱了……读者被带进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情境之中。 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解读出一个弗洛依德式的箴言——每个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女作家笔下的“俄狄浦斯”,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化了装”的“伊莱克特拉”? 作为昔日“先锋”,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格非的新作《不过是垃圾》也是篇“解构”性的小说,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死亡,就像个玩笑,更像是一种修辞,身患绝症的李家杰自知来日无多,生命、财富、公司等等都将不再归他所有,就连死亡本身作为一种修辞也失去了打动他人的效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可笑了。作为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大学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追到手的女同学苏眉。苏眉清高、倨傲,一尘不染,一直以来都是李家杰等一班“浊物”心中的痛。李家杰决定临死之前去看一看这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神,于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已经变换了的语境中又一次进行了“对话”,而“对话”的结果则是:苏眉被“做掉了”——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神,在300万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浊物”。而李家杰所得到的,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李家杰的感叹,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 罗伟章《奸细》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绕,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窝囊。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奸细”的,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相反地,他的做“奸细”倒真有几分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让他欲罢不能。做“奸细”不一定就是“坏”人,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好”人——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坏、忠/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当学校沦落成市侩出没的大集,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反智主义”时,一切的忠/奸/善/恶亦不再泾渭分明——中学已成为一个“洪桐县”。 教育的异化,是个一点都不亚于“底层问题”的问题。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教育”已与求知相悖,而几年过去之后,中学未见其好,反倒连大学也有些“中学化”了。小说《奸细》的文本,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有些“问题小说”的影子,但又超越了以往的“问题小说”。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问题小说”的种种“政治正确”的超越,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小说惟一的遗憾之处,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没能洞穿这一“反智主义”游戏的深层。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他以一种很“文本”的方式,向我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命案高悬》是一篇颠倒了的探案小说,一般探案小说的“叙事语法”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丝拨茧,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而《命案高悬》却把命案的真相“高悬”了起来,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复杂的倒是“体制”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正是本该作为“苦主”的死者的丈夫。小说中惟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既非公安也非侦探,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祸头”——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尹小梅却被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耐人寻味的是,吴响作为“体制”中的一名小卒时,尽可以去欺男霸女狐假虎威,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好事”时,不但被清除到了“体制”之外,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 致此,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高悬”。 《蚂蚁上树》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蚂蚁上树”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的“镜像”,是蚂蚁群、蚂蚁阵、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远看上去就有如“蚂蚁上树”一般渺小平凡。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黑压压一片”,而小说《蚂蚁上树》则“发现”并放大了这个“底层”群体,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 “底层叙事”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恰恰是因为以前“文学”对“底层”的漠视,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06年写“底层”的小说里,还有像曹征路的《霓虹》,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品。 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异,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不过,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05年末转载于06年初的《金陵十三钗》,也无法与之媲美。当然,有些东方“羊脂球”式的《金陵十三钗》也还是很不错的,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05年的12月份,就不便选进06年的小说中来了。还是那句话,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惟愿其长如源头活水,清且涟漪。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9
简介:本书为骆驼草丛书之一。选录作者中篇小说六部:《好大一对羊》、《徘徊望云湖》、《接吻长安街》、《飞来的村庄》、《北方、北方》和《土里的鱼》,其中《好大一对羊》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作品均以贫瘠的滇东北高原为背景,在描写那里农村艰苦、单调、落后的生活状况和农民愚昧、保守的思想的同时,表达了新一代农民思变的强烈愿望。作者文笔老道、深刻,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反映了存在于当今农村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比如,要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脱贫问题、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贫困人口与濒危动物共同生存问题,等等。
Zhaotong writers’ collection novel anthology
作者: 夏天敏主编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本书稿是《昭通作家精品集》之小说卷(中)。收罗了昭通老中青三代作家在一段时期的代表作品,基本上能够全面反映昭通作家近半个世纪来所取得的文学成就。
作者: 夏天敏等著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小说精选(木兰卷)》收入了十位著名文学作家的十篇代表小说作品 。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的描写感人至深的亲情,有的描写城 市校园生活,有的着墨于乡村悲欢离合,有的感知地域风物,有的描写缠 绵悱恻的爱情。《小说精选(木兰卷)》每部作品都生命的感悟,字里行间 蕴涵着的美和意境,让人回味无穷。
作者: 夏天敏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04月
简介:
《时光里的银子》是夏天敏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在作品中,收录了作家精心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时光里的银子》《绿碑》《七夕》等中短篇小说9部。夏天敏善于编辑故事,提炼主题。基本上在每一篇小说当中,作家既有诗意的描写,又有泼辣的口语,形象与心灵、结构与节奏融合无间。夏天敏的叙述语言百转千回,生动多彩,富有弹性,在乡土小说创作中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