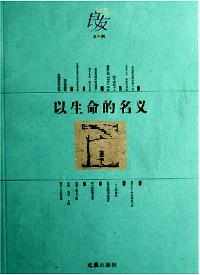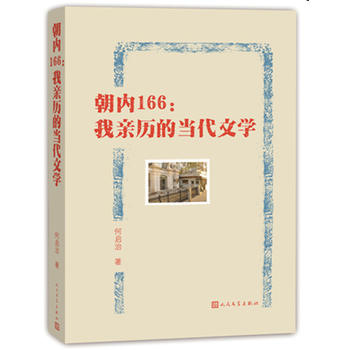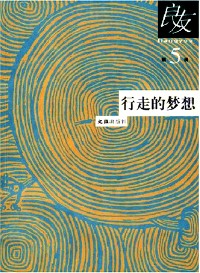共找到 10 项 “周昌义” 相关结果
- 全部分类
- 全部
- 文学
- 历史
- 哲学/宗教
- 法律
- 政治/社会
- 医学
- 教育/心理学
- 艺术/传媒
- 研究生考试
- 资格认证考试
- 公开课
- 语言
- 经济金融
- 管理学
- IT/计算机
- 自然科学
- 工学/工程
- 体育
- 行业资料
- 音乐
- 汽车机械制造
- 文档模板
- 创业
- 农学
- 生活
- 数据库教程
- 民族
作者: 萧关鸿,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7
简介: 《良友》丛书第4辑《以生命的名义》在坊间问世了,其风格自然仍秉承前边三辑的精神,惟一的不同,就是头题文章的主题不再是令人沉郁的死亡。在前边几辑《良友》出版后,我们不断接到读者朋友的来信,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疑问我们为何总是以沉重的死亡为开篇,尽管在《良友》第3辑的编辑札记里曾解释过这是因为源于《良友》丛书的宗旨: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坚强而脆弱的生命的关怀。并不是特意展现悲壮的死亡,而是因这悲哀的死亡令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和精神的重负。但是,读者的意见必然也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因此在本辑《良友》的开篇便换成了《文坛里的那些事儿》(1),以期给读者在阅读上有一个相对“轻松”的开始。 该文作者周昌义是《当代》杂志的小说编辑,作为一位推出了许多小说名家名作的著名编辑,因身居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这样的国中文学“重镇”,他的经历可以说见证甚至是参与了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或说小说主流的演变过程,因此他讲述的“文坛那些事儿”也就有了亲历者的档案解密性,况且,他当年曾以一部《作家忏悔录》剖析了当代某些作家的卑劣心灵和人生扭曲,也可以说“畅所欲言”是他的个性标志,这在他的这篇回忆里也得到了体现。因为他的回忆篇幅过长,我们拟分辑刊载,收在本辑里的是第一部分,主要涉及陕西几位著名作家,即陕西文坛当年的“三巨头”和“陕军东征”。 用周昌义的话说,当时陕西文坛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周昌义退掉了他苦心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周昌义所谈就是他亲历或见证的关于《平凡的世界》、《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长篇小说及给作家们带来的不同的命运故事。此文虽然读起来“轻松”,但内容并不轻松,尤其是,“三巨头”之一的路遥更是在《平凡的世界》之后,英年早逝。 相比于陕西文坛“三巨头”的壮怀激烈和长歌当哭,刘春的长文《北岛之后:事件与印象》则描绘了朦胧诗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诗人们的种种怪现象:杀妻自杀,卧轨自杀,杀人伏法,帮派打架,抄袭与“赞助”,性丑闻与裸体朗诵……是生活逼迫诗人走向了边缘?还是诗人自己“创造”了边缘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是一个话题,而本辑中的关于萌萌教授的两篇记忆则给出了思想与思想者的重量。作为一位中年因病去世的女教授,诗人气质的萌萌在她所属的哲学“群落”里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萌萌告诉我,大家所有的信件与图书资料都由她保管。我逐渐看清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精神团体,萌萌是团体的灵魂。所涉及的人与事都被融合进这个无形的精神团体。”(尤西林:《萌萌教授的精神遗产》)。《那个夏天,那个女生》让我们看到了萌萌从青春少女走向成熟中年的过程。 本辑中《城里的姨妈》讲述的是正常情景下的生老病死,“我”的二姨妈安静地走过了人生的晚年,但是,在作者摩罗的记忆里,二姨妈的一生又是怎样的非正常啊:死去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活。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 记忆往往是沉重的,而忏悔与剖析往往是为了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安稳。这也就是本辑中《以生命的名义》一文的意义所在。人在时代中的遭遇往往不能自我决定,但人在时代里的行为却往往由自我来选择。“满床厚厚的报纸,随着胖儿的每个动作咔嚓咔嚓地响着,因胎盘的脱落而再次涌出的血都没有浸透它们。等胖儿把所有的报纸卷成一团儿扔到床下,露出干干净净的床单,一点儿生孩子的迹象都没有留下时,留给我的便只剩下了沉默。”这是在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下的情景: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猝然出生了,在场的“我”沉默着,尤其是对她面临的死亡保持沉默。多年之后,“我”知道了——作为一个目击者,这样的沉默就是对杀婴的默许,也就是——很长时间使“我”内疚而又害怕承认的——杀婴的帮凶。这样的记忆和反省给作者德方的生活打下了抹不掉的烙印。与“知青”的往事记忆不同,逍遥的《被遗忘的“知青”部落》则描绘了“知青”当下的生活:曾扎根新疆的老于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把户口落于北京的。刚开始,退休金每月只有三百多,根本养不活他和上学的儿子。因为从小喜好艺术,老于对照相蛮在行。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个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去给游客照相…… 本辑中有一篇独特的书信,即蔡蕾的《本命年向世界首富求助》,作者的态度是坦率的,譬如:“父母是穷光蛋,我自己这么多年又没本事挣个新房子的卫生间。要我拿什么去讨老婆去生活呢?这工作吧,一提这工作我就要头痛就要哭……”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差异在类同中必然有着差异,但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他存在的意义,也许,这也是这封书信的价值所在。 《从北京图书馆出发》(李幼蒸)和《一个人的街道》(高瘦人)分别呈现了两种人生的自我努力的轨迹,在他们的记忆中,有忧伤,有苦闷,但在今天的回忆里,即便是痛苦,也带着淡淡的微笑,譬如高瘦人回忆他曾住过的老屋:前后曾有三个姑娘推开这扇门进屋去了,又拉开这扇门走出家门。她们是找我的,但最后都离我而去,与别的男人一起过上了别样的生活……对作者来说,初恋的甜蜜和失恋的失魂落魄都让曾生活过的老街老屋给吸吮干净了。 另外,本辑给读者端上的“私房菜”主要与女人相关,譬如作家韩石山的《但愿人间花不败》:“或许是因为品质,或许是因为经历,我一直喜爱女人,年轻漂亮的女人。这是个特殊的种群。山川因她们而秀丽,日月因她们而光辉。”因为喜爱,自然就有所谈。作为女人,阿琪的“私房菜”必然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出逃,私奔,失踪,其所谈也就增添了更多的理解:“曾经一起私奔的那几个月,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日以做爱的记忆,对她来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她说,一个人一生中有过这么几天,几个月,也就够了。”而对于失踪的女友阿萝,她今天再仔细想想,觉得阿萝真酷。
作者: 何启治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简介:
永生的忠实
23年前,长篇小说《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审稿编辑依次为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其单行本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首印14850册。如今,其作者陈忠实同志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热闹、喧嚣的世界,让我们想起来就感到无比的难过和忧伤。
我约请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始于1973年的冬天。那时我刚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北组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工作的重点。我在1973年的隆冬去找陈忠实约稿,既因为省作协向我推荐了他,也因为我刚看到了他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可供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当代》创刊于1979年)。在西安郊区工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就在寒风中向他约稿。在陈忠实听起来,这几乎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而我却强调《接班以后》已经具备了可以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陈忠实在农村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阅历完全可以做成,又以韦君宜亲自选定的两位北京知青(沈小艺、马慧)已经写成知青题材小说《延河在召唤》作为佐证。总之,陈忠实还是记住了我这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高门楼”来向他约稿的编辑。以后,我们时断时续地联系,他也始终信守着和我的约定。
到了八十年代,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初夏》几经修改,终于经我之手刊发于《当代》1984年第4期。陈忠实的《初夏》,可以视为他创作长篇小说之前必要的过渡。他的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终于,他可以向我谈及自己的长篇创作了。在1990年10月24日,忠实在给我的回信中谈道:“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书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不料学潮之后清查搞了几个月,搁置到今春,修改了一部分,又因登记党员再搁置。……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最后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作此事。”
我们当然对这未披露书名但倾注全力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1992年2月下旬,我接到忠实的来信,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们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到西安去取稿。忠实说,大约3月25日,“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谓益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就这样,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六位编辑的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白鹿原》面世迄今,累计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原版本、修订本、精装本、手稿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三十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总印数已达四百多万册,当不为过。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前辈评论家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娥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化为酒漏卮。”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汤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绝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海外评论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14期)
不必再征引了。仅此数例,可见海内外读者对《白鹿原》评价之高和反响之热烈。
据陈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十三部《白鹿原》的评论研究专著,单篇评论三百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跟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小说的基本要素来考察《白鹿原》。例如说,它有精心的结构,有诸如白嘉轩、鹿三、田小娥、朱先生等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有好看的堪称经典的故事,有个性鲜明的、有张力的语言,等等。
但是,推崇、肯定《白鹿原》的最重要的依据,我认为还是要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性、突破性来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对历史的反思是有空前深度的。《白鹿原》真实准确地描写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描写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半页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它通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书写,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都在风风雨雨、恩怨情仇中厮杀与折腾?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昌盛与达致现代文明社会?
社会历史在进步演变的过程中,会使人们对一些事物或一部重要作品有新的认识。关于《白鹿原》也同样有这种现象。1997年12月,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评委坚持要陈忠实对《白鹿原》作修订的两点意见,大约十年以后都有了不同的反响。
其一,是车宝仁在《〈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修订版删改原版2260多个文字符号,修订版比原版少了1900多个文字符号。对朱先生指国共斗争翻鏊子折腾老百姓的说法的修改,“显得生硬不自然”,“这里的修改很难说修改得很好”。对这种删改的合理性显然是存疑的。至于对性描写的删改,则认为“随着社会和时代向前推进,社会观念的变化,将来人们会更多地看重原版的价值。此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出版时一些人批评其性描写,而新世纪以来已未见此类批评,也能说明读者评论家观念的推进。”(参见《说不尽的〈白鹿原〉》第712页—7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其二,是陈忠实自己明白无误的表述。关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鏊子说”,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限,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的表述。……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面对有人认为“鏊子说”表明作者缺乏智慧的批评,陈忠实的回答是:“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为继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引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陈忠实毫不含糊的反批评的态度再鲜明不过了。
我不可能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排序做正式的调查,但最近我在相熟的评论家、编辑和作家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如果要排个座次,你们认为谁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呢?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白鹿原》当之无愧地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如果再按二三四五排座次,那意见分歧可就大了。
2012年5月,我又从到延安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的评论家朋友白烨那里,听到关于《白鹿原》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地位的信息。其一,据说在深圳某报举办的包括网络、电话等形式的评选活动中,在“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影响*的30部书”的评选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即拉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二,是南京的某大型文学刊物邀约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评论家评选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毫无争议地当选。
这些信息,可以说起码没有出乎我的意料。高大全式的人物和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却肯定是有的。
自1988年4月起笔写《白鹿原》,陈忠实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每周,他回城一趟,从家里带吃的馍回到白鹿原下的祖屋里,靠着冬天一盆火、夏天一盆凉水写作。屋门前十米手植的一棵梧桐树,从大拇指粗长到胳膊粗,有了可以给主人遮挡阳光的绿荫。梧桐树见证了陈忠实写《白鹿原》付出的一切艰辛。为了完成《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不知经受过怎样的心灵的煎熬,付出多少心血与牺牲。石家庄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给陈忠实的信里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
所以,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和我的同事们说过,一个编辑,一生中能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我的幸运。关键在于你遇到这样厚重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不管有多少争议都是无法回避、绕不过去的作品)时,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要敢于为它拍胸脯、做保证,甚至立下“军令状”,愿与这样优秀的作品共荣辱,与它的作者同进退。
陈忠实当然是重友情、讲信义的作家。对我,对咱们《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相识、相交以来,一直如此。
2012年5月,我和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之邀访问白鹿原。我们参观陈忠实文学馆,在思源学院白鹿讲堂讲课,在白鹿书院座谈、题辞,到原上采摘樱桃……老朋友聚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
其间,陈忠实和我商讨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事。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初步的方案,如章程草案之类。我曾建议就以“陈忠实”冠名,他却以“白鹿”取代了自己的名字。
我回到社里便向当时的社长潘凯雄和总编辑管士光报告了。他们俩都表示积极支持。其后,潘凯雄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白鹿奖”的事便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
2013年1月7日,由社长管士光主持召开“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委会。评委还有付如初、赵萍、杨柳和我,参与其事的还有当时的社长助理——我们戏称之为“秘书长”的周绚隆。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奖项、获奖者名单和有关事项的安排。
3月20日,因健康原因极少外出的陈忠实亲自来到了北京,和管士光一起向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编辑颁奖。颁奖会由新到任的主持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应红主持。何启治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特别奖”;刘会军、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于砚章、王建国、刘会军、刘海虹、刘炜、刘稚、包兰英、王鸿谟、许显卿、杨柳、脚印、周达宝、周昌义、胡玉萍、彭沁阳、赵水金、何启治等十七人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特殊贡献奖”;杨柳、孔令燕荣获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前三项其实就是奖励二十年前组织、编辑、出版《白鹿原》的有功人员,以及奖励《白鹿原》面世二十年来人文社在出版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则从现在起两年评选一次,奖金由陈忠实提供,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经费则由人文社负责,奖励人文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借以激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不断提高人文社当代文学原创作品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我最清楚,陈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是对咱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真感情的大作家。新闻界、文学界对此也是认同的。“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会后,经媒体广为报道,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这里的“一”当然只是泛指的数量词。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去年10月23日,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刘稚到西安去看望病中的陈忠实,给他带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10卷本《陈忠实文集》(包含他的所有文学作品,共380多万字)。不久,又看到了邢小利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正式面世。我想,这些对病中的忠实都是一种安慰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0月24日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十分沉痛地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把忠实与鲁迅相比,但就应该懂得拥护、爱戴、崇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出类拔萃的杰出、伟大的人物来说,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好在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爱戴、崇仰我们的大作家陈忠实。
书比人长寿。精神的影响比物质的东西更深远。
有陈忠实的作品在,有《白鹿原》在,陈忠实就是永生的。我们真挚的朋友、我们敬爱的大作家陈忠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永远活在千千万万读者之间。
是的,我们一定会记住永生的陈忠实。
啊,白鹿远行,呦呦鹿鸣。精魂犹在,长留人境。
2016年5月1日
写于寓所北窗下,其时我的视力已下降至0.1。
作者: 桂国强,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8
简介:《良友(第6辑):幸福天上寻》可以说是中国半个世纪的生活缩影,从50年代的“反右”(民主统战人士的遭遇)、“文革”、青海建设兵团、到“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80年代的“理想年代”,直到当下的生存状况,尽管每个人的记忆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但却都真实地呈现了每个不同年代的历史烙印,“幸福天上寻”这个书名也就有了另外的寓意。《良友第6辑:幸福天上寻》有两篇长文,一篇是《机关大院的故事》,一篇是《〈读书〉十年1987》。前者三万多字,后者七万多字。前者记叙的是北京一个民主人士生活的大院里的故事,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在作者张华的记忆里,“大院中活着的长辈已寥寥,曾经的玩伴不少也都离去。他们却始终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一幕幕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看多了,心凉了,内心刻满深深的恐惧,犹如不愿做的噩梦始终徘徊难去,偶尔还会将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后者是原《读书》编辑扬之水当年的日记,尽管题目标明是她在1987年的日记,其实还有一个小小“引子”:日记是从1986年12月15日开始的,因为那一天她正式去三联书店上班,第二天就到了《读书》编辑部。1987年的日记也是到12月15日,对作者来说,正是她在《读书》十年的第一年。正因为是“《读书》十年”的第一年日记,意义自不同后来,从日记所写的详细和态度上,当和“习惯了此一工作”应有所不同。“老沈一清早来送稿子,并以本期几篇稿子为题,向我大谈《读书》的办刊宗旨,反复强调: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又和他一起往赵一凡家贺乔迁之喜,编辑部的几位先到了,赵一凡的夫人正坐在楼梯口的油锅前煎藕夹……”这是作者的一则日记的片断,从这片断里当可读出扬之水1987年《读书》日记的特点所在:真实性和可读性。等于以《读书》为舞台,80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周昌义的《文坛那些事儿》(3)在该辑里是其长篇对话的尾声了,主要谈的是关于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出版过程和《当代》如何处置王蒙的长篇小说《疯狂的季节》。从周昌义的调侃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人文社大牌编辑如何把握和操作一部小说的故事,尤其是“为什么要出”和“为什么不能出”的区别,而他的对话也时时一针见血,譬如:出版社出书,第一看市场,第二才看好歹。《尘埃落定》遭遇退稿的时间,应该是1995、1996、1997那几年。还记得不?《废都》和《白鹿原》及陕军东征是在1993年。那以后,长篇小说有了赚钱的可能。但对于大多数作品来说,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绝大多数作家,还只能自费出书。还有,《废都》和《白鹿原》开拓的纯文学市场,只适用于《国画》和《沧浪之水》这一类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不适用于现代主义先锋们。《白鹿原》对于火爆了近十年的现代主义先锋们其实是丧钟,那以后,一切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维和正常人的口气讲故事的这主义那主义都被正常人视为“神经”,开始了永无休止的盘跌。九七年前后,恰恰是他们最凄凉的时候,坚持跟他们一起“神经”的期刊都开始了跟他们一起凄凉的绝路…… 如果说周昌义所谈是人文社如何出市场叫好的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么,戴煌的《一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则性质和意义完全不同。戴煌所回忆的是自己写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与出版该书的过程。1998年5月,该书第一次印刷就达15万册,各地的盗版就更多。但该书的出版却是充满了波折,在作者的记忆里仍记忆犹新: …… 《良友》第6辑的书名“幸福天上寻”来自书中的一篇作者署名为“苦丁”的文章,该文副题“表妹武真的寻梦路”。武真是2008年1月28日在北京不幸被抢劫遇害的年青记者,苦丁的这篇回忆记叙了武真从一个在济南读书的大学生到去北京寻找她的理想的成长历程,但在文后,苦丁的心情更是矛盾的:因为想到武真,我更多地被悲痛占据着。写到现在,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写这样一个文字了。记录伤痛,记录绝望,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但是,我还是忍着悲痛写了。而写了这么多废话,却不能表达我对表妹武真的悼念之万一。只好还是引用《中国经营报》武真的那些同事们为她写下的悼念诗歌,来表达我对武真的痛惜与悼念吧:“再见,我们的玫瑰,永恒的24岁。生命在严寒中凋谢,事实让人无法忍泪。天真的笑靥,绽放的青春。一切的美好,永恒的24岁……” 该辑《良友》中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这就是蔡朝阳的《我所认识的范美忠》。汶川5?12大地震后,“范跑跑”成了网络上的“明星”,更成了教师道德底线的争议“标志”。这篇蔡朝阳的“旧文”告诉了我们范美忠如何“一路走来”,在蔡朝阳的描绘里,“失败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如何面对“物质生活”,又是“为什么流浪,流浪到远方”,这一切也昭示着从“网友范美忠”到网络上的“范跑跑”有着内在的存在逻辑和生长缘由的。而傅国涌的《“语文小报”与我》则记录了他成长年代的一段珍贵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追求者的成长档案。 另外,《急诊科医生的手记》(陈阵)、《父亲的工棚》(吴佳俊)给我们留下了当下社会的个人记录,民间与底层的生存总是在“证明”着文学虚构的苍白和无力。王立玮的《向西,向西,向西》所记录的是当年青海建设兵团里的青春悲剧……
作者: 桂国强,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8
简介: 《良友》第5辑的一个重要看点是张北川的《一门学科和一个行者》。 本辑有两篇是来自海外女学者的文章,其一是李南央的《丹麦老人格珍 》,其二是沈睿的《多丽丝·莱辛的中国行》。 本辑《良友》里的《一把不肯生锈的刀子穿过天空》和《“突然死去的 人是残忍的”》则是对诗人自杀事件的剖析和揭秘。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 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 的进步。”这是徐宗懋之所以写《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的缘由 。 周昌义的《文坛那些事儿(2)》所讲述的是关于王跃文与《国画》当年 风云一时的故事。 张梦阳的《洛矶山下的刘再复》细致地记录了今日的刘再复在美国的生 活状态:“从功利的牢房,概念的牢房中挣脱出来,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 是诗意的存在。” ……